《可怜的东西》剧情介绍
影片基于苏格兰作家阿拉斯代尔·格雷所著同名小说,融合现实主义、奇幻、科幻元素,将弗兰肯斯坦的故事重塑,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逃避丈夫虐待却不幸身亡的女子贝拉(艾玛·斯通 Emma Stone 饰),在被科学家成功复活后,心智停留在孩童阶段,却也对未知世界充满渴望;她与放荡律师私奔踏上挖掘自我的冒险,试图摆脱时代对女性偏见,追求平等与性解放。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反诈风暴我黄金光辉的人生埃洛伊塞纳妾记第一季古墓迷途极速生活为梦想发车@互联网人被遗忘的爱钻石迷情残酷的彼得西村京太郎悬疑剧场十津川刑警的肖像5镰仓电铁杀人事件幽灵世界异水情劫怒海劫运最后约翰死了乘船而去死侍2:我爱我家石榴坡的复仇富家穷路第一季关于命运目光所及再见夏天乐坛毒舌嗡嗡鸡第二十季抵达之谜穿粉红色裤子的男孩毒镇鹈鹕的故事爸爸别走
《可怜的东西》长篇影评
1 ) 更适合奥斯卡宝宝体质的女性觉醒电影
兰斯莫斯既不具备对人性的精确观察,也似乎对角色不抱有任何程度上的共情。
他的电影所显露的,只不过是一种徒具其表的古怪,和一种撒泼打滚式的反叛姿态。
今年的十部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作品中,《可怜的东西》是在IMDb和Letterboxd上除《奥本海默》外评分最高的一部,也是最晚上线流媒体的一部,再加上威尼斯金狮奖、英国电影学院奖影后、金球奖影后等奖项的加成,让国内影迷对这部电影吊足了胃口。
但它的最终接受度却出人意料:上线三天后,《可怜的东西》的豆瓣评分就已经从8分跌到7.4分,甚至比不过几部春节档本土大片。
与此同时,本片的IMDb评分也在降,但0.1分的降幅远没有国内情况夸张,影片依然位居影史250排行榜单的中部地带。
说到底,这种对同一部影片的接受度差异,反映的依旧是文化差异。
国内观众对《可怜的东西》的批判,大部分集中在性别层面:一部由男人执导,由男人编剧,由男人撰写原著小说的女性觉醒题材电影,怎么可能真正触及女性意识核心?
更何况主演艾玛·斯通在片中还有大段大段的裸戏和性爱场景。
综上所述,这部电影一定充满了男性影人对女性演员的“男凝”和“PUA”,而艾玛·斯通则毫不自知地成为了被男性影人剥削的工具,和女权运动的叛徒。
以上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严格去相信这个叙事,未免显得过于天真。
首先,艾玛·斯通在好莱坞的资历要远远胜过导演欧格斯·兰斯莫斯或是编剧托尼·麦克纳马拉。
当艾玛·斯通在2012年正式成为蜘蛛侠女友时,希腊人兰斯莫斯还没拍出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当艾玛·斯通在2017年首次问鼎奥斯卡影后时,兰斯莫斯的好莱坞敲门砖《圣鹿之死》也还在后期制作中,再等两个月才会在戛纳首映。
其次,在《可怜的东西》中,艾玛·斯通与兰斯莫斯一起出任制片人,深度参与关于影片的种种创作决策,并非是在拍摄过程中被导演任意摆布的可怜人,她也在颁奖季采访中屡次澄清这点。
所以,相信石头姐在本片中任人宰割的观众们,要么是太过低估了石头姐的好莱坞地位,和她掌控生涯的主观能动性,要么就是太过高估了兰斯莫斯在好莱坞的地位和能量。
此外,凡是见到由男性主创的影片中出现女性裸露镜头,就想到“剥削”二字的观众,思维模式也未免过于简单。
分析任何影片对女性的态度,都要从整部影片的语境、肌理和场面调度等方面具体入手,若是只套用简单的思维模式看电影,那么最终看到的所有电影都会像自己一样简单。
即便说了这么多对于《可怜的东西》反对意见的反对意见,但我依然认同反方的部分观点,尤其是对艾玛·斯通表示惋惜的那些——她为这样一部肤浅幼稚的电影做出如此牺牲,实在有些不值,虽然身为影片制片人的她,或许也是这些肤浅幼稚的始作俑者之一。
《可怜的东西》是对弗兰肯斯坦故事的某种重写。
外形可怖的科学家戈德温(威廉·达福饰),本身就是其父种种违背伦理的科学实验的产物,而继承了父亲实验精神的他,又通过在刚刚死去的怀孕母亲的脑袋里植入其胎儿大脑的疯狂方法,让这位自杀的独立女性死而复生,同时拥有成年女性的身体和幼年女性的心智,这种奇妙反差为影片的开篇部分制造了许多笑料。
影片的开篇部分由黑白影像呈现,极佳地复原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风貌,而实验产物贝拉与她的“造物主”戈德温,以及与文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的种种张力,也很值得拿来大做文章。
如此故事设定,既能让我们想起《可怜的东西》的灵感来源之一《弗兰肯斯坦的新娘》(1935),也能让我们想起像《野孩子》(1970)与《象人》(1980)一样,讲述边缘人如何在导师的循循善诱下,与文明社会产生接触的电影佳作。
倘若《可怜的东西》愿意在这条道路上深耕,那么它可能会变成一部更具深度也更能触动观众的电影。
但这显然不是导演兰斯莫斯的意愿。
兰斯莫斯一直是个试图在人类行为中发现虚伪和滑稽之处的冷眼观察家。
他眼中的人物大多是动物本能的奴隶,却总要借助种种堂而皇之的话术与姿态包装自己,于是在这些外衣崩塌时,他们就会显得格外可怜可笑。
这也是《可怜的东西》中超广角镜头(俗称“鱼眼镜头”)频频出现的原因。
部分观众会在其中看出色情片惯用偷窥视角的影子,但我相信这并非兰斯莫斯的本意,因为在少数没有女性角色出现的男性角色对峙戏码中,他同样采用了这类镜头,制造出一种戏谑夸张的视觉效果。
在我看来,这种视觉手法指代的是一种来自导演的生物学观察目光——导演就像显微镜另一端的科研人员,或是水族馆窗玻璃另一端的看客一样,饶有兴味地观察着作为生物的人类的种种可笑可悲,并在对这些生物的嘲讽中获得满足。
但我怀疑,兰斯莫斯在面对其角色时具备的优越感,仅仅是来自他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信,而不是来自于阅尽世间百态后得出的可靠思辨结论。
从《圣鹿之死》到《宠儿》再到《可怜的东西》,我们一直能从他所采用的广角摄影、推焦镜头和美术设计风格中,看到库布里克的影子,而库布里克标志性的反人类基调,似乎同样也是兰斯莫斯试图模拟的对象。
问题在于,兰斯莫斯对库布里克的模仿仅仅停留在表层。
库布里克某种程度上的反人类倾向,是基于他对自己作品中角色深入而精确的观察,而在厌世基调的背后,你也能感受到库布里克对人性怀有的深深悲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将自己从人类群体中排除开来。
反观兰斯莫斯的创作,你既没有从他的角色身上看到他对人性的精确观察,也无法看到他对角色抱有任何程度上的共情与关心。
他的电影所显露的,只不过是一种徒具其表的古怪,和一种撒泼打滚式的反叛姿态。
《可怜的东西》也不是例外。
如果说同样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女性题材电影《芭比》是头脑聪明却佯装幼稚,那么兰斯莫斯的电影便是头脑幼稚却假扮聪明。
从贝拉简单粗暴的意识觉醒和成长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人物层次,也看不到任何对女性意识细微之处的敏锐把捉,相反却看到了许多在几十年前便已过时的关于“性自由带来头脑自由”的陈词滥调。
《芭比》中玛格·罗比在长椅上与老太太对望的几个镜头,胜过《可怜的东西》洋洋洒洒的140分钟。
男性影人创作女性题材电影不是原罪,即便是《芭比》,照样在幕后有着男编剧诺亚·鲍姆巴赫的强力输出。
如果兰斯莫斯愿意真诚地反思男性群体在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中犯下的失误和可以改进的空间,或者像《芭比》一样,承认男性同样也是男权秩序之下的受害者,《可怜的东西》也会成为一部更加发人深省的作品。
但他同样没有做到这点。
《可怜的东西》中的诸多男性角色,从马克·鲁法洛饰演的花花公子(一个更大号也更扁平的Ken),到克里斯托弗·阿博特饰演的将军,再到威廉·达福饰演的科学家(达福用演技尽力补救了角色的单薄),要么坏得陈词滥调,要么好得陈词滥调,导演丝毫没有理解人物处境并探索其所思所感的意图,于是最终只能造就一系列卡通式的空洞讽刺形象。
影片的架空背景同样是一大败笔。
虽然片中人物的服饰与姿态都来源于19世纪英国,但在里斯本段落中出现的蒸汽朋克风格城市景观,似乎又把故事背景推向了未来,而这种设计的唯一意义,就是让故事发生的年代被架空,并进一步使得影片的所谓批判性表达更加无指向可言。
于是片中那些看似激进的大尺度场面和挑衅言论,在架空的背景下只不过是对着虚空打靶。
这或许也是兰斯莫斯有意为之的“聪明”选择:他将不会因此冒犯到任何具体的人。
好笑的是,正是这样一部制作精美,姿态前卫,内核却无比空洞羸弱的电影,在今年奥斯卡角逐中获得了11项提名,远超《芭比》。
作为电影,《芭比》有属于它本身的问题,但任何有头脑的观众,大概都能看出一点:它的某些表达是言之有物的,并且不可谓不激进。
然而学院却最终更偏爱像《可怜的东西》一样的电影:有着激进表象,实质上却包裹着保守甚至落伍的古早价值观。
这大概也是好莱坞对年轻影人和女性影人的一种隐性规训手段: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表达,但这种表达最好按我们已经约定俗成许久的规矩来,最好不要冒犯到任何具体对象,且最好是空洞无物的。
如此这般,好莱坞便既具备了支持女性独立的表象,又没有真正在头脑层面让女性群体清醒过来,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一切依然可以按照既定的法则运转。
一个多么伪善的系统,而它催生的又是多么圆滑聪明的投机分子。
你不小心的话几乎会为之鼓掌。
2 ) 没人想阉割你,别焦虑了
用电影表达社会议题,是创作者的义务吗?
从传统影迷的角度来看,繁琐的社会价值观似乎成了绑架影像的枷锁。
所以如果一部影片有意识想要为一个主义背书,就天然地要求一个掌控力强大、能有机地将艺术风格协调入理念表达的创作团队出现,在这一点上,希腊导演兰斯莫斯大约做到了五分之四。
我们先来谈谈这部影片真正的缺点,最大的一点,是全篇的叙事太“功能性“地围绕着女性主义这个”核“而展开。
无论是威廉达福还是未婚夫麦克坎道斯,这些配角无论男女,都太工具化了,就像一根大骨头煮得太烂以至于上面的肉都挂不住了,艾玛斯通就是这根最硬的骨头,而其他角色无论男女,都可以戏剧性地出现而后消失,任人差遣,且功能性的借角色之口说出的教育意味台词,也使得全片对现实的攻击性大大降低,因此影片之外很少有《芭比》那样的破防潮,这个弗兰肯斯坦的故事更像是一则寓言,重剑无锋,戳不破脸面。
第二缺点,则是编剧团队在编写许多段落时的俗套化处理,其实本片虽打上了喜剧tag,但实在难以称之为优秀的喜剧,最明显的就是威廉达福前半句说一大堆专业术语,未婚夫让他请说人话,他就说自己”阳痿而无法上她“的喜剧设置,这些段子已经俗的不能再俗了,编剧团队理应使用更具天真意味的编排,符合影片的基调。
说到此处,关于这部影片最核心的一点也应声而出,这部电影为什么激怒了这么多中国女性观众,让艾玛斯通承受如此多的性场景拍摄真的不是在剥削女演员吗?
关于这点的矛盾,其根源其实是中国女性观众对于手握权力的陌生感。
影片与《钛》类似,给出了一个人工造成的新生命,一个“赛博格“,这是具有强烈反叛色彩的存在,虽然贝拉只是人脑移植的产物而并非完全由人造出,但通过人工违背天伦对生命体的复现显而易见是在挑战自然的、宗教的旧秩序。
在这一点上,兰斯莫斯主要使用了两点方法论,其一,服化道的反向生殖崇拜,《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的极致形式应当由一名巨大化的婴儿来饰演主角,不过无法成行,那么就让一名成人女性穿上婴儿的巨大服装吧!
一个婴儿却拥有成年人的力量,行走在街上,藐视人们建立的一切秩序,所有伦理纲常应声瓦解,成为被嘲弄的对象。
石头姐的维多利亚风格衣服,正像加大版的婴儿套装,其褶边的形状也恰好与女性生殖器的形状对应,而在法国街头的窗户形状,则是倒过来的男性阳具,在库布里克的价值观中,一切人物由生殖欲望控制,脱离不出自然的大手,而兰斯莫斯则告诉我们,”人“自己是最主观最伟大的,我们可以改造自然,也可以藐视自然给我们的欲望,这不是枷锁,而是权力。
第二个方法论,就是镜头,首先兰斯莫斯不是一个搞噱头的白痴,影片的美学布景由景深镜头展现,意思就是,除了近景的人物特写之外,中景和远景的物体都在运动着,有意义地服务于叙事,观众的双眼可以在画面上尽情游走,这是最基本的平权而非引导。
鱼眼镜头的作用则是在告诉我们人物处于天真蒙昧,秩序尚未建立的状态,所以在开篇的英国时期,镜头畸变被大幅应用,而随着人物的笃定,她从痴呆儿变成了GOD,秩序已然建立,人物有了力量,影像的掌控权来到贝拉手里,归于和谐与沉寂。
再说性爱场景,这里的核心观点在于,你们的说教不管用了,你们的歧视不管用了,拯救妓女的途径不再是圣化卖淫,而变成了“这是我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隐喻表达,用来言说一个道理,让任何人建立自尊的唯一方式,是让他自己成为评价他人的那个主体,其余一切暴政与迫害,都最终沦为客体,是被看的对象。
于是在本片中,男性的阳痿与早泄得到嘲笑,男性的性羞耻和处女情结得到嘲笑,这是一种言语上的暴力,但同时也呼应了那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而贝拉击败那个难以逃出的父权城堡的方式,是用一把手枪,击穿了剥削者的血肉。
因此,在意女演员演绎性场景的观众也无需焦虑,那些男演员的软糯阳具才是被摄影机着重审视着的,片场上也有很多专门的工作人员实施保护。
《可怜的东西》,佳作!
3 ) 整个电影院只有男观众笑了
这个标题导致收到很多“女观众”也笑了的评论,有点无奈,但不打算改,因为说到底我只是在陈述一个我经历的客观事实,并以此为一个引子来表达我个人对这个电影的看法而已,虽然“到底谁笑了”对评价一个电影的社会影响来说确实有客观价值,但并不是我的重点,也不会影响我看这个作品时的主观感受。
我当然知道全球所有看了这个电影的女性们不可能一个都没笑,我当然也知道只是我看的那一场正好如此而已。
—————电影出现“笑点”(Bella的各种犯傻)的时候整个放映厅只有男人在笑,我只觉得浑身不舒服。
说到底,这里面所有的笑点都符合大男子主义想象——一个美丽但单纯笨拙的特别女性。
女权主义不是性解放,在男权框架下谈性解放是无比可笑的,那只是满足了男性把世界变成妓院的性幻想。
女性主义是关于女性可以作为主体去解读这个世界。
影片中Bella的主体意识构建的过程让人质疑,她一直被关在家里,一半是孩子一半是实验工具,她的思考就靠看几本书,瞥了一眼贫民窟惨状并精神崩溃但完全没有帮助他们(我知道她给了钱,可显然她的钱没有给出去,以及就算给出去了,一视同仁的给钱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愚蠢的方法),她唯一的工作经验在妓院……最后她回家,Max告诉她,我不会在意你做了妓女,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OK,在此她获得了她的未婚夫的包容,于是步入婚姻殿堂。
可是那时她依然还是个幼儿脑,依然还是个比较早熟擅长思考的孩子的样子。
Max还问她有没有查过性病,所以这个架空设定里依然是做妓女有很大健康风险的啊?
那为什么没人为她健康着想?
一个是只在乎自己男性尊严的前男友,一个是无底线纵容的未婚夫……她的创造者上帝甚至在她路都走不好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了Max,that’s fucking sick,这不算精神恋童癖吗?
电影想探讨女性特征是被规训出来的,可是,解放女性也并不是靠放纵。
更深刻的东西,剧情并没有触达。
整个故事里我没看到一个成年人的历程和觉悟,最后Bella眼神中透露的阅历以及她的整个成长路径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
于是最后我只觉得看到了一个死了爹继承家业,弄疯前男友,把前夫变成羊,且有个纵容自己的丈夫的开心小孩,得意又安逸的和女朋友坐在曾经一直想逃出去的院子里看书。
以及,最近看了好几个影视剧里,都出现男性一脸痴迷的对女性说,你很特别,以至于我对这个表达都有点ptsd了,“你很特别”听上去真的很像什么古早gaslighting technique,欣赏你捧高你孤立你三部曲之类的所有给Bella人生转折的也都是男性,创造她的,引诱她的,启迪她的,包容她的。
全片那两三个女性角色说话的不痛不痒程度几乎是符号化的。
尤其是被过度美化的妓院生活,很难不让人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就是一场男权框架内的直男恋童癖式智性恋+各种对女科学怪人的kinky幻想。
豆瓣某个给这个电影打出高分的影评给Bella贴了个“性欲过剩”的标签,同时又说这是一个“更聪明,更能令全性别观众接受的(女权电影)”,另还有人在影评中一边称赞电影一边称Bella为“性瘾者”...真的非常讽刺。
Well,所以全性别观众都能接受的女权电影就是有大量裸戏,美化妓院,把妓院塑造成一个想开就来想走就走对女性没有身体精神伤害,方便女性沉思哲学并获得自由的地方是吗?
以及“性欲过胜”?
什么是性欲过胜?
谁定义的什么是正常什么是过胜?
她的行为在医学鉴定上完全称不上是性瘾或者性欲过胜。
电影里律师虽然不是啥好角色但也能承认“男人的不足”,怎么现实中......算了,难听的话不想讲了。
很失望。
奔着蒸汽朋克暗黑风芭比的噱头去的,看完以后觉得,虽然我对芭比观感很一般,但别用这个碰瓷芭比了。
4 ) 男性脑子里想象的女性寻找自我追求平等,我作为女观众观影全程只想报警
影片一开头,一个成年老男人和一个智力不正常的成年女人的设定,就已经让我想报警了。
毕竟我作为一个现代人,影片再怎么宣传奇幻色彩和年代久远,你都知道这种设定不会是对女主友好的环境,正常人都能看出其中的危险之处。
女主的设定是一个成年女性但是被替换了婴儿的大脑,为了显示女主的婴幼儿属性,特意安排了一段她站着尿失禁而毫不在乎的片段,这段着实没必要,因为没有这段,不论是剧中的医学生还是观众都看得出她智力水平不正常。
而且因为有这一段,我反而比较好奇,既然是成年女性的身体,为什么不是展示她来月经经血顺着腿流下来呢?
然后就到了女主突然性觉醒的剧情,这段就真的特别男性视角,因为女人都知道,女性无意识的性觉醒是从夹腿觉得舒服开始的,如果我们的大脑没有被灌输纳入相关的内容,我们是不会有想要纳入的想法的,因为阴道内部没有神经,女性的性器官是阴蒂,阴蒂才是女性性快感的来源,所谓的阴道高潮本质也是阴蒂高潮。
但是女主在没有性教育的情况下刚性觉醒,就想到要把黄瓜放进阴道,这就真的只有男的才会愚蠢的这么想。
邓肯第一次遇到女主的时候,用手触碰了女主的性器官,这是性骚扰行为,但是显然男主创认为这是在对女主的性启发。
在现实生活里,任何男的跟智力异常的女人发生交配行为,正常人只会觉得这是性侵,因为智力异常的女性不懂何为性同意,也不懂没有避孕行为的交配行为会有什么后果。
影片前面都是黑白,开始转向彩色,是女主第一次和邓肯发生纳入式交配行为,这也是典型的男性视角。
女性如果要通过性觉醒而从黑白世界进入彩色世界,那也应该是她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性高潮,而这部片子的情节应该是她自己摸自己的时候,而不是跟男人纳入的时候。
影片最荒谬的就是女主为了了解世界自愿去当妓女进入剥削女性的行业,为了体现女主的自我意识,还安排了女主对老鸨要求应该是妓女选客人,这样妓女才能获得快乐。
我的天,大概只有男人才会认为女性这样想就是自我意识成长了,他们大概想不出女性真的自我意识成长是要彻底废止这种剥削女性的行业的。
当然老鸨并不会听从女主的话语,所以还是客人选妓女,但是女主发明了一系列手段,比如跟客人讲笑话听客人的人生故事跟客人玩游戏,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男人对女人的性剥削。
男性找妓女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rape,所以男性创作者的这些情节就真的是特别可笑。
主动被性剥削永远不会是女性寻找自我争取平等的手段。
影片有大量的交配场景,但是没有任何避孕的行为,女主也没有怀孕,也没有她为什么不怀孕的任何解释,你说神奇不神奇。
🤷🏻♀️🤷🏻♀️🤷🏻♀️🤷🏻♀️电影从头到尾,就是女主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再到另一个男人,她生活里的女人特别少,少数的她遇到的女人,都没有给她任何真正的属于女性的建议或者讨论。
唯一在她做妓女之后问她有没有做健康检查的是一个男的。
这部电影不是真实的女性故事,全片都是男人想象中的女人,而且在合理化现实里让人想报警的行为。
我看过对《可怜的东西》最荒谬的评价是,有女网友说因为女主心智不成熟,所以没有性羞耻感,所以才能在妓院探寻世界。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正是因为她心智不成熟,所以她不懂什么是性强迫性骚扰,她也不懂什么是性同意和可以拒绝。
因为不懂,所以她最多也就只能对老鸨说应该是妓女选择客人以追求快乐,但她不会跟老板说妓女应该有拒绝的权利。
她被男人粗暴对待时,她知道自己不舒服,但她不懂拒绝。
她跟老鸨谈论这段的时候,老鸨对她说有些男人就是喜欢女的痛苦,她也只会觉得奇怪,而不懂这是性强迫是不对的行为。
5 ) 长评 | 主体性假象
文 / 阿崽排版 / 唯唯封面设计 / 脆脆鲨全文约5100字 阅读需要13分钟 未来已经到来。
兰斯莫斯和他的新作⼏乎预演了未来电影最糟糕的⼀种可能性。
当AI已经能够充分模拟⼈类躯体运作,以架空的世界观来为绚烂过度的造景开脱,所有的道德⾯向都能够在⼤数据下计量出平衡的解法,《可怜的东⻄》诞⽣了。
⼀部扼杀了每⼀丝空⽓、周密⽆死⻆地包裹着塑料薄膜的电影,以及⼀次将电影作为⼤型极权机器运作的展演。
在这个意义上,《可怜的东⻄》的确是⼀部了不起的寓⾔。
这个巨⼤谎⾔狡猾地为⾃⼰找到了⼀个看似安全的⽀点——⼀副⼥性的身体,Emma Stone 的身体。
在单⼀视⻆的统摄下,这具身体似乎获得了“主体性”,性别议题被轻松安置进了⼀个能够链接普世情感体验的架构。
但请永远别惮于怀疑那些打着“成⻓”旗号的电影,因为所有能够被拍下的成⻓轨迹都需要被仔细甄别,那究竟是真正发⽣于⼈物的身体当中,还是仅仅摹写着作者规划好的⾜迹。
The Night of the Hunter (1995)那些我们愿意称作童话的电影,通常承载着我们更多的信任感。
尤其,在那些⿊暗显得极其深邃的童话⾥,观众和主⼈公更是有⼀种宿命般紧密的连结。
然⽽这温情的同⾈共济并不是观众⾃主选择的,⽽是有限地被赋予的,因为童话极端的情境设置使犹疑尚存的中间地带⼏乎完全被抽除了。
以这种信任感为前提,观众⾃愿向历险的主⼈公让渡感官的主动性,允许主⼈公代替⾃⼰去知觉,陷⼊⼀种【被动】的情境。
这的确会带来令⼈着迷的沉浸感,甚⾄可以说,这恰恰是⼀些电影具有强⼒的主要原因,因为被凝聚起的信任,以及作为忍受这种单调的回报,影像在某⼀刻能够⾃在地迸发出奇异的能量。
并且这信任的交付绝不意味着放弃主动思考。
童话确乎以其对事物本质的抽象化提纯了世界的维度,但⼀个诚实的创作者绝不会希望将童话世界的抽象与现实的具象⼀⼀对位。
在那些最好的作品⾥⾯,即便观众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主⼈公,却总有⼀些时刻发现⾯前的⼈物深不可测,ta像是脱离了所有可循的来源,发展出了⾃⼰的思想。
于是我们得以不断发现着我们与主⼈公的距离、童话世界与现实的距离。
Blue Velvet (1986)⽽当这种信任被利⽤——简直易如反掌:⼀个孩童般纯洁的主⼈公(如果是⼥性就再好不过)、⼀个陷⼊困境的弱者,踏上⼀段缤纷的奥德赛之旅,途中有“⿊暗”将她不断推向深渊的边缘,再在终点处以⼀个⼤⾏动作为成⻓的独⽴宣⾔。
只消把视⻆减省,⽤奇观化的视听语⾔营造⼀种“你正以主⼈公的眼睛看世界”的幻觉,就有⼤批观众愿意出让主动权,因为惰于思考、全盘接受创作者的掌控简直是最轻松愉悦的观影体验。
在视⻆绝对的统摄⼒之下,Bella 仿佛被赋予了⼀种“主体性”,⽽成⻓路径也像是被内化为了她的主动选择。
可是这之后,我们通过 Bella 的身体看到、感受到了什么呢?
我们可曾真正进⼊过她的视⻆呢?
“当你在拍摄如此神秘的东⻄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觉得⾃⼰是个骗⼦呢?
任何情况下,最好问⾃⼰这个问题,并以某种⽅式将这个问题纳⼊我们拍摄的内容中;但怀疑毫⽆疑问是彭泰科沃及其同僚们最缺乏的。
”[1]
从对婴⼉-⽊偶的摹仿到经历了对性欲、⻝欲的发觉,作为⼈类的身体性逐渐复归,说到底,兰斯莫斯和 Emma Stone 试图发明⼀种被牵绊的身体存在姿势,以此来隐喻⼥性在⽗权制结构中的困局,并将其作为影⽚整个符号系统的依托。
再加上对哥特童话暗⿊⻛格的浅薄想象,我们看到了⼀种“⾮⼈”式的表演——试图将对⾃⼰身体的控制贯彻⾄每⼀个关节、每⼀句⾔语,对“被牵绊”的展示在极端的控制下变成了⼀种丑陋的僵直和残缺。
尽管影⽚早早给出了⼀系列前史:绝望的前世、被改造被监禁的重⽣。
但经历了怀孕和坠落之后,肌肤仍然光滑,身材仍旧完美。
所以其实并不是 Bella 的处境塑形了她的存在姿势,她的身体是被抛⼊虚空的⼀具实验品,和电影⾥成堆被所指绑架的图像⼀样,从未成为姿态,只是毫⽆灵魂的图像的修辞,困在虚伪的辩证法⾥徘徊。
最重要的,这具身体没能保有任何⽆法被探知的秘密。
吃东⻄就表演好吃,喝酒就表演醉态,做爱就始终表演着快感,穿着⾐服却也像在众⼈⾯前⾚裸地敞开。
⼀切都能够被观察到、被解析,直⽩得如同电⼦元件。
我们甚⾄看不清她急于再吃上⼀⼝的⻝物⻓什么样⼦,只看到吃进去时的表情,和极速变焦的性爱场景特写⼀并被简化为欲望机制的图解。
⼈们什么也没有感受到,⼈们只是不断地被告知。
或许在⾥斯本,⼀阵歌声(即便被处理了做作的混响,有着真正⽓息的声⾳)短暂地越过矫饰的雕栏流淌了出来。
但看着镜头逐渐推近,Emma Stone 被框定在景框正中央的脸庞以最⼤幅度竭⼒演绎着“⽬瞪⼝呆”,我们要如何相信这歌声真正抵达了她的身体呢。
在这过度外化的表情背后⼏乎不存在任何的深度。
⽽⼀个真正具有主体性的⼈物,⼀定有着超脱了剧本甚⾄影像的,⽆法被任何⼈测知的神秘。
回想那些真正令我们感知到身体苏醒的电影时刻。
在《⾼、低与脆弱之间》的开篇,从⼀场⿊夜的暴⼒中逃开,我们随着露易丝迈步向世界的清晨。
沉睡了五年的身体,轻如新⽣的理想。
⻦鸣。
⼀点亲肤质地的柔粉⾊,穿过⽇常模样的街道,来⼩摊买⼀个双球冰激凌。
街道对⾯的镜头随着露易丝平⾏地横移,横移,经过了⼀棵树的遮挡,随即带⼊了纵向的另⼀条街道,后景顿时开阔,我们的⽬光有如跟着镜头⼀起伸了⼀个懒腰。
没有AI作画般缤纷的⾊彩,也⽆需刻意制造⼀种陌⽣感,甚⾄⽆需将镜头推近。
但我们的确感受到了空⽓的温度和流速,也辨认出了⼈物此刻毋庸置疑的、新⽣的姿态。
Haut bas fragile (1995)然⽽尽管如此形容,这绝不是⼀个没有重⼒、完全轻飘的场景。
请留意露易丝⼿⾥⿊⾊的旅⾏包——显⽽易⻅的重量使她的⼀只⼿臂⽆法⾃如地摆动,轻浅的步伐也不得不调整⾃身,与之⼩⼩地对抗。
因为这⼀个旅⾏包的重量,我们看到了⼀种与重⼒抗衡着的⾛路姿态,⼀种呈示着⼈物处境的姿态。
⼀具身体从沉睡中【回到】这个世界,携带着⾃身的历史。
历史没有沦为⼀种象征主义的陈词滥调,⽽是化作了牵动着⼈物躯体、组成姿态的多义的⼀点重⼒。
在《⾼低脆》⾥,阴霾绝没有被扫除,危险和阴谋始终存在、交织为⽹格。
⽽重⼼的拉扯未被呈现为⼀种跛脚的残疾或歪斜,因为“重”不是对“轻”的否定,“轻”也没有简单地化归为对“重”的消解,两者之间构成了⼀种清晰的平衡。
于是暗⾊不曾搅乱明媚的舞,肢体得以在⻛中舒展出⾃身的空间。
听到歌声瞪⼤眼睛的 Bella、半睁着眼死去的 Godwin、变成⼭⽺⽬光呆滞的将军,每个⼈物轮流陪兰斯莫斯上演着不cut坚决不眨眼的游戏——“再坚持⼀下啊,⻢上就推到⼤特写了。
⽜逼⽜逼”。
在声声的⿎励中,这种连睫⽑末梢都能保持⼀动不动的静物扮演,俨然成了这个剧组的⾄上信条。
操纵摄影机制造着浮夸变形的“视听语⾔”,⽆节制地放⼤、审视着每⼀具残疾的身体,以感官体验之名,⾏剥削⼈物之乐,⾃作聪明的“发明实验”变成了兰斯莫斯炫耀权⼒的表演。
镜头运动的轨道是否对于兰斯莫斯来说更像是游乐场的过⼭⻋轨道?
⼀切运动和速率的流变都被奴役,成为服务于瞬时⼼跳的傀儡。
⽽坐在轨道上那个涂装成维多利亚⻛的塑料⻋厢⾥的恐怕只有兰斯莫斯本⼈,滑稽地以成年⼈的身躯挤进,佯装身处⿊暗童话。
当 Emma Stone 本⼈声称⾃⼰并未被剥削,是否意味着我们该对这部电影试图控制⼀切的欲望视⽽不⻅?
在原著⼩说当中,Bella 在探索世界的旅途中渐渐也开始了对于⾃⼰身份的主动探寻。
为什么在影⽚中 Bella 经历了欲望和智识的觉醒,唯独质问“我是谁”的⾃我意识觉醒被省略,仅仅作为⼯具促成了结尾处混淆视听的⼀次和解?
假设那段疯狂的舞蹈真的能够开辟⼀条怪异但朝向⾃由的通路,为什么影⽚却放弃了这种极端的身体⾛向(这难道不更贴合他想要的暗⿊⻛格?
),反⽽转向了后段“正常”的回归?
⼀切如此了然——⽆论是婴⼉头脑性感⾁身的芭⽐娃娃,还是智性加冕后禁欲式的施虐狂,这具身体不过是坠⼊了餮⾜男性欲望的另⼀个端点。
这个虚假的世界从未⽣成过真正的逃逸线,Bella 始于家宅⽽终归于家宅的环形“成⻓”轨迹,完整写就了兰斯莫斯从施虐到受虐的欲望频谱。
⽽兰斯莫斯显然对此毫⽆⾃觉:“她(Bella)承认她会累、会受伤,但她会继续前⾏……我认为《可怜的东⻄》是我最积极的电影、最充满希望的电影。
” [2] 听听影院⾥男性观众的笑声吧,如若这部电影真的有指向过某种现实,为何从不曾激起哪怕⼀丝的痛感?
“……他们是野蛮⼈,但不是不可容忍的,只要多⼀点智慧、精明或耐⼼的话,我们应该就能够逃脱惩罚。
与此同时,每个⼈都逐渐习惯了恐怖,这⼀点逐渐融⼊⼈们的⽣活习惯,很快就会成为现代⼈⼼理景观的⼀部分;下⼀次,谁会对不再令⼈震惊的事情感到惊讶或愤怒?
”[3]在此,我依然想尝试说明本⽚与《芭⽐》的差距。
由于芭⽐作为⼀个塑料玩偶⾛向⼈类社会的路径和以 Bella 的身体为依托的成⻓譬喻⼗分相似,两部影⽚似乎不可避免地被拿来对⽐。
⽽两者最⼤的区别就在于,《芭⽐》清晰地知道⾃身作为商品的局限性,⽽选择了极致扁平的路径。
她创造了⼀个虚构的乐园,但绝没有让形式沦为批量⽣产假象的⼯具。
创作者的姿态源于对⾃身有限的⾃觉。
在介绍 Barbieland 时,摄影机虽然⼀直跟随着 Margot Robbie 所饰演的“刻板印象芭⽐”,但观众的视⻆更像是在玩具店的橱窗外,有距离地观看着⼀种纯粹的虚构。
之后⽆论是芭⽐意识到了死亡、发现了橘⽪组织和脚跟落地,还是来到了⼈类世界之后的情节设置,也都没有被呈现为“真实”对虚构的渗⼊,影⽚的表现依然是扁平化、卡通化的。
也即,《芭⽐》并没有在未清楚呈示⼈物处境时就借由“⼤⼥主”视⻆的便利营造出⼀种主体性幻觉,⽽是不断地提醒着观众⾃身的虚构。
这正是缘于葛⻙格⼗分清楚,这具于乌托邦⾥被虚构出的完美塑料身体不可能具备现实的主体性,并且始终觉知着这部电影本身和现实的距离。
这之中唯有⼀个独特的时刻。
当芭⽐坐在⻓椅上,凝神感知和⼈类共同的回忆。
她睁开眼,第⼀次,观众真正分享了芭⽐的视线,和她⼀同感受到了现实世界的空⽓——我们感受到了⼀种真实,不单单因为听到了⻛声和⻦鸣,更是因为,芭⽐此刻真正地将⽬光投向了他⼈,看到了这个原本以 “我”为圆⼼构建的世界上“我”之外的存在。
这些存在不取决于任何⼈的意志,也没有为了引起惊奇⽽畸变为图像的奇观,仅仅作为⽇常⽣活中随处可⻅的⼀隅,被看⻅。
⾄此,芭⽐和我们共享着的⽬光真正纳⼊了现实的⼀瞥,作为芭⽐开始追问“⾃我”的坐标,也作为《芭⽐》在和现实世界的距离间定位⾃身的坐标。
这样说或许有偷换概念之嫌,但如果《芭⽐》真的带来了感动,也许是因为葛⻙格的努⼒并不在于让观众去共情芭⽐,⽽在于让芭⽐,⼀个活在真空世界的⼈偶,去共情作为⼈类的我们(她们),以及哪怕⾮常有限地,去涉⾜我们的处境。
她⿎励我们去看那些电影之外的事情。
《芭比》中Real World一瞥⽽与之恰恰相反,《可怜的东⻄》的扁平却意图遮蔽观众的感官和思考。
从始⾄终操持着最浮夸的语⽓,故作⾼深地昭示⾃⼰洞穿了⼈类社会真相,⼀边占据着“虚构”的⾼地,⼀边却不断兜售着愚蠢的隐喻,⽣怕观众看不出来影⽚跟现实的对位关系。
以虚构为名的扁平不过是⽤于掩盖对性别议题浅薄的认知。
每⼀次情节即将导向更深刻更幽微处之时都被有意打断,似乎害怕观众的头脑真的开始运转。
《芭⽐》深知阴道不存在的假设悬置了危险,《可怜的东⻄》却精明地想象出了⼀具完美性爱机器:有阴道但没有⽉经和性病,也不⽤担⼼会怀孕。
想想这样的身体会被男性创作者们形容成“⾃由的祝福”,真是令⼈⼀阵胆寒。
这⾥不存在真正的⿊暗。
⽆论充斥着多少怪异奇诡的元素,都只带来了令⼈发笑的奇观。
那些被⻛格化的暴⼒、被刻意丑化的男性⻆⾊,都展现着能够被忍受的可憎⾯⽬。
当电影成为暴⼒⽣产隐喻的符码,在同⼀的控制之下,不管是被反复强调的“⾃由”,还是奇观化的暴⾏,不都是通往致使⼈麻⽊的终点吗?
兰斯莫斯和他的全男编剧团队如此迫切地要为⼥性代⾔,简直恍若美泰⾼层开会——他们只是把⽗权制藏得更好了。
当然,看到这⾥或许还是⽆法说服你,因为⼀切都可以在浅显的⼆元论中找到为⾃身开脱的答案: God 既是背德的渎神者,但也是被⽗权阉割的慈爱家⻓;Max 恋童但阳痿,还是从⼀⽽终的纯情⼥权男;Bella 要有⼀种天真的邪恶,杀死⻘蛙、破坏⼫体不能眨眼,因为这是不受社会规训的游戏。
但也要读书,要对底层展现撕⼼裂肺的同情⼼。
可读书救不了世界,所以还要去做妓⼥,⽤⾁身丈量世界的深渊;既要展现主体性,要复仇,但不能和⽗辈决裂。
如果你还不满⾜于此,就是压根没看懂前⾯庞杂的隐喻;如果指责他窥淫,“这是医学观察和媒介⾃反”;指责他恋丑,“这是以戏仿讽刺⼈性丑陋”……然⽽,这“既是”“⼜是”的两端藏匿了多少虚假的道德?
“善”不但仅仅只是对善的演出,更是对恶的粉饰和开脱。
⾃问⾃答的逻辑闭环⾥,唯独不存在⽣成思考的缝隙。
⽐起精明的圆融,我们难道不更应该呼唤⼀种偏执的真诚,哪怕这真诚难免冒犯?
如果说电影仍是“⼈的艺术”,没有被技术所占领的话,那么我们则永远应该赞美那些“有限”,赞美那些毫⽆保留的脆弱、怀疑,和势必不完满的多义。
引用:[1]论卑鄙——[法]雅克·⾥维特 翻译:Leviathanism[2]Yorgos Lanthimos on Poor Things :Sight and Sound interview By Nicole Flattery[3] 同 [1] 评分表
往期推荐评论翻译 | 论新观众长评 | 被倾注的清晰的岛屿访谈翻译 | 潘佩罗电影小组的奥德赛:从《非凡的故事》到《迷雾中的她》
6 ) 这部大尺度新片,重点真是“女权”吗?
自打问鼎金狮以来,电影《可怜的东西》在颁奖季上一路披荆斩棘,不仅在金球奖上成功挑落竞争对手《芭比》(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更是一举囊括11项奥斯卡提名(仅次于《奥本海默》的13项)。
《可怜的东西》和《芭比》均被视为女性电影,但后者在奖项上不如前者耀眼接下来的奥斯卡影后角逐中,石头姐(艾玛·斯通)的赢面很大,凭借“巨婴”到女性主义者这一不可思议的蜕变,她已先后荣膺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英国电影学院奖、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倘若能够再次斩获奥斯卡影后,她将复制七年前凭借《爱乐之城》完成的壮举。
艾玛·斯通在金球奖上而较之评论界不遗余力的表彰,《可怜的东西》在影迷群体里却引发了不小争议。
很多人质疑:电影披着女性主义的外衣,却在镜头和情节设计上行“男凝”和“剥削”之实——尤其体现在毫不节制的性爱场景和妓院戏份中。
难道:只有通过不停和男性做爱,女性们才能觉醒?
这是怎样直男式的无耻意淫!
我觉得这种思路,主要来自对影片大尺度画面的误解:马克·鲁弗洛饰演的邓肯和那些奇形怪状的男士,各个身材堪忧、形象猥琐,可他们的床伴却是瞪着一双无辜大眼的美女石头姐,这好比一朵鲜花不停插在一堆牛粪上......加上欧格斯·兰斯莫斯将性爱场面拍的兽性十足、毫无美感,自然会令很多女观众感到被冒犯。
我想:倘若跟石头姐床战的不是绿巨人而是高司令,一众妓院嫖客也没有那么丑陋,“剥削”、“伪女权”的指责声或许会不会小一些呢?
性事双方形象的不对等引发的恼怒心态(还需考虑到演员的名气和地位:一方是奥斯卡、金球双料影后,另一方的嫖客尽皆无名之辈),使人在解读电影时易陷入两个方向:一是以现实逻辑去套这部完全被架空的非现实电影,二是基于成见而引发过度的脑补。
对贝拉主动卖淫的指责,就是套用现实逻辑。
我当然同意妓女是被剥削的存在,卖淫是对女性系统性的社会压迫而不能是个人简单的自主选择。
但当我们就此情节发出质疑时,已经脱离了具体电影:贝拉从设定上就不是一个正常女性,她未经社会化洗礼,又怎能从社会的“高度”权衡卖淫利弊?
何况《可怜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基于真实社会的故事,而是幻想一段历史上的“平行时空”。
贝拉选择卖淫亦出自经济利益的考量,邓肯抢光了“上帝”留给她的钱,她要如何独自在巴黎生存?
女性主义也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独立的重要性——所以,妓院戏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反女权”。
只能说它的呈现方式有欠妥当。
而“过度脑补”则体现在对大量性爱场面的耿耿于怀。
其实性爱并非贝拉探寻自我的旅程中的唯一启发,相反却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因此,并不能说“整个电影基于女主从插入式XX获得快感这件事”(某瓣高赞短评)——这完全是误解。
我们不妨仔细捋一下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贝拉初尝性快感,靠的是男人么?
不,她是靠自己——也就是无意中发现了自渎的妙处。
贝拉是率先发现了性,之后才“发现”了男人。
所以,并不是男人“启发”了贝拉性的快乐。
而且从男人身上,贝拉更多感受到的是不快:邓肯无法满足自己,而妓院众生更令她滑向自己所谓的“轻蔑愤怒”。
这种不快在贝拉与邓肯大战过后发出的灵魂拷问中表露无疑:邓肯:男人无法做个不停。
贝拉:这是生理问题吗?
男人的弱点?
邓肯:嗯......或许吧。
这段话讽刺地揭示了男人的虚弱。
不管他们嘴上吹嘘自己多厉害,却无法满足女性的欲望——特别当这种欲望是没有羞耻心的、未经社会驯化的原始欲望。
在这种欲望面前,男人们往往望而却步或者缴械投降。
因为男性惯于以欲望主体自居,当他们发现女性居然能够“反客为主”时,就会感到尴尬和恐慌。
男性对自身的欲望从来都毫不收敛,却以“合不合礼”来压制女性的欲望。
只有那个黑人小哥直言不讳地说出:“有礼的社会,会毁了你(女人)”——欲望的双方并不平等,贝拉却要求平等。
这才是对贝拉“性欲过剩”的正解。
男性对女性欲望的规训话说到这,你大概可以原谅影片中的那些性爱场景为什么如此激烈肮脏了:这纯粹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兽欲发泄,一点都不平等——明明对方只能疲软地来三下,还要被“教育”说违心话“棒极了”。
兰斯莫斯正是希望这些“不公平”的场景令你感到反胃,生怕你产生看A片时的“代入感”。
相反,在拍摄贝拉自渎场景时,兰斯莫斯就没有暴露什么身体部位,他一直将镜头对准石头姐的脸,直抵高潮。
似乎是想表达:想获得真正的快乐,还不如“自给自足”。
想想看:是不是这么个理?
所以我才会说:影片中的肉搏戏虽多,却不重要。
再举一个交媾不重要的证明:“性欲过剩”的贝拉,其自身却是“单性生殖”的产物。
维多利亚能变成贝拉只因“上帝”给她换了脑子——这是理智“分娩”的结果而与下半身无关。
这一脑子本来就蕴藏在母体中,“既是母亲也是女儿”,而更绝的设定是:创造贝拉的“上帝”还是个性无能者......没有性能力的“上帝”依靠科技和自身的理性来造人,而“繁衍”人的器官居然是大脑——理性和知识的缘起。
在这一反人类的设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兰斯莫斯相信性是原罪,“更高级的人”应该有更高级的诞生方式,这流露出他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绝望......所谓的“上帝”或者说兰斯莫斯自己,大概对人生是持以这种态度:人或许不该出生,但既然已经存在,死也没必要。
所以“上帝”会拯救自杀身亡的不幸女人,但又对自己的选择充满纠结: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痛恨人生到选择放弃甚至永不回头。
如果她从空虚的永恒中被拖回来......我凭什么决定她的命运呢?
但我本身也有一项认知,我的研究已进展到这一刻,命运赐给我一具死尸以及一个活体婴儿......
这番拧巴矛盾的内心剖白说明:“上帝”不认为自己“换脑续命”的行为一定是对的。
而是既然摊上了这样的命运,只能被迫承受......以下两部电影,便有助于我们理解《可怜的东西》真正想表达些什么。
第一部是赫尔佐格的《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男主角说过一句话:“来到这个世上对我来说是个可怕的堕落”。
1974《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与贝拉相似,卡斯帕尔·豪泽尔一开始也被“父亲”锁在房间里与世隔绝。
两个人的大脑也都不“正常”。
不同的是:作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贝拉凭借着好奇心、主动大胆地闯入文明社会并向其发起挑战,最终赢得了自由,找到了自我;而卡斯帕尔则是被动地被抛入人类社会,最终被文明世界放逐和绞杀。
《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另一部电影是大卫·林奇导演的《象人》,该片同样涉及社会的边缘人(畸形)、医生、精神病院等元素。
林奇同样批判了“文明人”的虚伪与残酷。
和《可怜的东西》一样,纵观全片,里面最像人的,反而是那个最“不正常的人”。
1980《象人》说到这,《可怜的东西》这一片名的真正含义便呼之欲出。
谁可怜呢?
表面上看,是身不由己的贝拉可怜。
“上帝”说她可怜,就连她自己也认为自己可怜。
可如果兰斯莫斯是这个意思的话,那片名就该叫《Poor Thing》而不是《Poor Things》。
而“Things”是“thing”的复数。
这便一语道破天机:可怜的何止贝拉一个。
同样被父亲掌控、身残志坚的“上帝”可怜;被人群排挤、视作异端的助手马克斯可怜;自大、暴躁又脆弱不堪的邓肯也很可怜......妓院那群拥有各种古怪性癖、连自身欲望都难以排遣的家伙,更可怜。
更不消说,贫民区里那些像狗一样被暴尸户外、无人问津的可怜的死婴了。
可怜的东西:可怜的人类。
在兰斯莫斯看来,所谓“人类社会”不过是冷漠、虚伪又残酷的“文明人”彼此逢场作戏的一出“大戏”。
每个人都对周遭的真实和真相熟视无睹、对谎言和不公习以为常,活在这样的世上,才是最可怜的。
船员私吞贝拉对穷人的捐款贝拉在邮轮上邂逅的黑人小哥哈利,便凝聚了影片对人类文明的批判。
哈利指给贝拉看贫民窟的死婴,不光囿于阶层批判,而是指出:貌似和谐有序的社会本质,是弱肉强食的吃人盛宴。
你看弱者很可怜,可“如果双方位置对调”,结果也是一样。
哈利被老妇人称作“cynic”,意即愤世嫉俗者。
他最大的愤来自:人之异于禽兽者几何?
所以他坚信理性无用、坚信知识无用,“我们这个物种没救了”、“哲学只是人们想逃避我们都是猛兽的事实”。
不止哈利一人这么想,影片很多地方都在暗示人与禽兽的边界并不那么明晰。
譬如“上帝”在解剖公开课上就公然宣称:“谁能区分人与禽兽?
假如其中有差别的话。
”
回想尚处在“婴儿”阶段的贝拉,对人想打就打、想摔东西就摔东西,行为与小兽无异。
当她第一次看到青蛙,第一反应是“杀了它”(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虐待蜻蜓、蝴蝶等小动物的行为);可随着贝拉对人性和社会的了解与日俱增,再次面对船员虐杀海鸥的行为时,显得若有所思。
从杀害青蛙的残忍到面对死婴的潸然泪下,贝拉对生命的态度慢慢发生改变了。
她通过自身的经历和实践证明:同理心是需要“培养”的。
因为可以“培养”,所以说人性本身也未必有哈利所想的那么残忍。
“如果了解这个世界,就能改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学习和经验是有用的。
逐渐认清社会的贝拉是看透社会的哈利的对立面存在,在她看来:后者爆棚的负能量,不过是“无法承受世间痛苦的伤心小男孩”的逃避之举。
他不是她理想中的那种人。
那要靠什么方法才能避免来自文明社会的荼毒和同化,成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我”呢?
兰斯莫斯给出了他的答案:贝拉光怪陆离的奇幻冒险,高度浓缩了人这一生成长的四个阶段:一、经验哪怕是被禁锢在深宅大院里,贝拉也拥有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这点至关重要。
不管性、美食、喝酒还是舞蹈,哪怕沦落到妓院,贝拉都是主动出击、主动选择。
她绝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
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上帝”看起来与邓肯的控制欲颇为相似,总以“外面的世界不安全”为由阻止贝拉去探险,其实并不然。
他主要是以科学家的理性预防实验对象出错,在深层价值观层面,“上帝”亦崇尚经验。
否则,他也不会向贝拉倾吐如下的心声:他们(编造的贝拉父母)是勇敢的探险家,因为山崩死在南美洲,他们大胆挑战极限,付出代价,人生那样才有意义。
有意义的人生一定是勇于实践的人生。
因此,当贝拉明确地告知“上帝”再不让自己出去将会恨他的时候,“上帝”便遵从了她的自由意志。
大致说来,“上帝”代表了兰斯莫斯心中理想的父母:因自身遭遇过父辈的强迫而尊重子女的主体性,避免了悲剧的延续和轮回。
子女并非温室的花朵,以“爱”之名为其打造一个安全屋是行不通的。
二、知识和艺术食和性属于本能的范畴,按马斯洛的理论,当生理层面的最低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一级的追求就会出现。
影片中显现为知识和艺术。
但说实话,不论是聆听楼上女子高歌还是阅读爱默生,贝拉成长中的这一关键“进阶”都刻画得太仓促了。
普及一点爱默生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贝拉的转变:爱默生推崇直觉,重视个性和心灵的价值,批判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拜金主义——这些思想很契合了贝拉的人物特点和后续作为(捐赠)。
三、同理心叔本华曾将人类行为的动机分成三种:希望自己快乐、希望别人痛苦、希望别人快乐。
简要地来概括这三种动机,便是利己、恶毒和同情。
利己和恶毒都是非道德的,只有同情是真正的道德行为。
贝拉看到死去的穷人时流下伤心的泪水,意味着她的“道德自觉”。
先前的她,只有利己和恶毒(譬如既享受邓肯带来的刺激又想将他扔进海里)。
直至面对众生的苦难,她才将心比心地认识到人之为人的艰辛。
这也直接影响到她后来对邓肯的无能表现出宽恕,并主动迈向妓院品尝底层的“人生百态”:不经历一番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同理心便无从建立。
然而,就像知识和艺术施加于她的影响一样,贝拉的“道德自觉”也展现得异常突兀和刻意。
这三个概念在兰斯莫斯的手里,真就成“概念”了:它们出现的时机无法与前后情节水乳交融,好似为了凸显人物变化而适时强行插入的文字说明和注解,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弧光。
所以看惯了一般剧情片的观众就难受在这儿:这哪是人物啊?
这不是大段说教么......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想:贝拉就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她本来是“一张白纸”,歌曲、爱默生或贫穷这类“小事”,给她心灵留下的印记当然比“一般人”要大。
正如:你对自己童年的印象会记忆犹新,因为一切都是新奇和放大的。
四、历史追问贝拉最后选择“回归”家庭、“报仇”前夫的戏码则可以这么理解:她终于能够直面自己。
对自我的反思、历史的反思属于最高级的智性活动,这意味着贝拉真正的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她只想弄清一切的前因后果,明白自己从何处来,才能知晓未来将向何处去。
给前夫换羊脑的本意并不是报复,而是自保。
她是在继承和践行“上帝”留给她的科学和理性遗产,仅此而已。
在对贝拉的冒险旅程仔细梳理过后,我们会发现:《可怜的东西》是通过一个幻想中的完美女性来教你做人。
用一具本来最“没人性”的生命体的进化,来反衬“正常”人性的可怜与可鄙。
超越世俗污染的、凌驾于文明之上的“理想人性”究竟什么模样才是影片探讨的重心,女权主义尚在其次。
所以,“女权-伪女权”的争论,甚至怀疑兰斯莫斯是不是在故意“辱女”实在是跑偏了方向。
其实《可怜的东西》并不费解,只是它凭空搭建的那个世界和女主角“超越人性”的人性,让早已习惯现实主义议题的观众不习惯。
若非优良的视听与置景,恐怕更多人难以忍受。
要我说,它真正的问题在于表达过于生硬甚而浅显。
影片的深度包不住它天马行空的设定,而它呈现的“理想人性”也并没有构成一份明确的答案。
它提出问题,却无力解决。
当然,又有谁能解决“人性”呢?
作者| 纪扬;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7 ) 长评区说这电影不懂女权,其实是自己不懂电影
刚学会个词就瞎用。
导演是男的——男性凝视。
女性角色裸漏画面享受性爱——歌颂放荡,倡导乱交。
女主个性鲜明作风怪诞——男创作者的性幻想。
女主角体验生活做风尘女子——高知阶层体验生活,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等等。
男性角色认可了女主的选择——这是怜悯和谅解我们不需要。
看完长评区就这个感觉。
害,其实说啥都不懂是一个夸张手法,这是我个人无法认可的观影逻辑。
描述等于鼓励,角色的悲喜等于价值导向,以一种阅读课本的姿势走入影院。
好像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很多人的防备心很重,像买东西的时候带着一杆公平秤,一定要看看男的占多少分量,他们对这个分量是怎么看的,他们是不是满足了,他们怎样看待女性角色在剧情中做出的选择等等,要我说,这都不重要。
我当然认同向下的自由不是自由,性解放不能带来真正的权力反转,当妓女是一种被迫的、有害的甚至是绝望的处境。
是的,性的部分只是关于女性地位的一小部分,但我同时也认同:表达或阐述女权主义的文艺作品,没有统一的纲领,唯一正确的主题,正向的纯粹的完美作业。
如果有,那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暴政?
我同样欣赏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人生经历,不过在那部其真实故事改变的作品中,主角一生优雅知性,家庭美满事业有成,难道只有这才是传说中的“真正的”女权电影?
何尝不是一种窠臼之谈。
《可怜的东西》中,我看到了一个看似危险的概念,那就是“没有羞耻感的女性”。
有趣、悲伤、放荡、美丽。
她在人们面前自慰,谈论欲望。
她在想探索世界时和陌生男人一起出逃,好奇“过去的历史”时勇敢放弃一切去明知危险的地方寻找答案。
在一趟如此奇幻旅程中,她未曾因男人的说教而自我怀疑一秒,未曾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犹豫和委婉分毫。
这个时候观众朋友说:我看到了一个男人,和他的性幻想。
不能不说是一种可惜吧。
片子用将近两个半小时的时长描绘了一次瑰丽的探险,我们跟随天马行空的镜头游历里斯本、远洋航行、希腊某处和落雪的巴黎,在某些人的眼中:女主什么都没干,只是去做了妓女,天啊她竟然去做妓女,如果这是男性创作者的女儿或姐妹会愿意她们做妓女吗?
天啊,对此我只有一句:到底是谁在关注男的怎么想?
要清楚地看到:《可怜的东西》并不关心女性在现行社会中,像处于一场劣势的棋局一样,如何运用智慧和策略适应和生存下来的。
如果带着这样的眼光去审视——那么做性工作者当然不是一个好选择。
它有点像蒸汽朋克、性转版的弗兰肯斯坦,探索并挑战社会支配和压制女性行为的方式。
贝拉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平行的过去,一个充满哥特式风格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个因社会中父权权力不平等而扭曲的世界(兰斯莫斯运用了大量鱼眼镜头,呈现的扭曲的画面让观众们有一种类似孩童的视角)。
这部电影是对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的颠覆性演绎,贝拉的创造者和监护人由非正统的天才戈德温·巴克斯特博士(威廉·达福)扮演。
贝拉称呼他为“上帝”,他的脸上有着奇形怪状的伤疤,是他童年时期父亲疯狂的科学实验造成的——但这种经历并没有阻止他对科学实验的巴洛克式追求。
戈德温招募一位学生助手马克斯·麦坎德尔斯(拉米·优素福饰)来记录贝拉的进步。
但贝拉对知识和经验的渴望太过贪婪,无法被限制在戈德温宅邸的围墙内。
她接受了流氓律师邓肯·韦德伯恩(马克·鲁法洛)的邀请,开始了一场自我发现之旅。
从伦出发,先到里斯本,然后乘轮船到亚历山大,最后到巴黎的一家妓院。
随着贝拉视野的开阔,影片的视觉效果也随之改变。
主要以戈德温的家为背景时,画面是黑白的。
但贝拉冒险出去后,就变成了彩色。
那种调色设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现实的质感,每一帧看起来就像手工着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印着色情作品的明信片。
《可怜的东西》拥有专属于兰斯莫斯的特质,鱼眼镜头、非传统取景、从丰富的黑白到饱和的色彩的转变),像是一场动乱。
编剧和配乐也很好地适配贝拉一路的探险故事,微妙的失衡之感带观众走进这个怪奇旅途的幽微之处。
但是,就像《宠儿》一样,让这个片子更加惟妙惟肖独一无二的部分归根结底来自于表演。
斯通的英国口音,以及演变过程——从一个充满欲望的女人(酒、性、蛋糕、跳舞)到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设定自己的社会道德,并决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人。
尽管旅途中多次遭遇规训,试图让贝拉接受男性的目光,但她因无法感受到羞辱或羞耻而让那些既有的社会现实轻松被击碎。
她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时尚、性、良知和慈善:一切为自我的感受服务。
片中贝拉一头黑发衬托出她苍白的脸庞,身体经常暴露在外。
这个角色如果是其他人饰演可能会引起观众的怜悯,或者产生一种不安的剥削感。
但由于女主坚定的下巴、野性的双眉、和对灵巧的身体的控制(她疯狂舞蹈和摇摇欲坠地醉酒部分表演中可以看到基顿级别的技巧),片中的每个包袱最后总是转向那些试图驾驭贝拉的男人,他们愚蠢、自私、有时又丑陋懦弱。
这样有趣、悲伤、放荡、美丽的混合物。
这奇幻的、光怪陆离的,坦率的作品。
归根结底,《可怜的东西》是一个关于女主角开辟自己独特道路的旅程。
贝拉的个人意志得到充分体现和解放,不能不说是一个真正激进且女权主义的童话故事。
8 ) Poor Things 可憐的東西:生命的本質是自我的探索並為自己而活
不得不說非常對我胃口,本質上我就很喜歡這類極具創造力、天馬行空的怪胎電影,也讓我深深折服於Yorgos Lanthimos的腦袋,這樣的劇本、如此高的完成度、詭異的配樂、迥異的風格,屬實「怪才」無誤。
一開始真的讓我想到《科學怪人》,導演應該有借鑑它的點子來發想這部電影,正是這樣的「怪」一步步帶我們進入貝拉的世界,跟著她一起探索世界。
觀影過程中我無數次感覺自己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被挑戰,嚴格來說是我感到被挑釁了,導演打破了符合主流價值的哲學觀與神學觀,貝拉遇到的人都有自己一套獨特的觀點,不管同不同意都必須認可這是一個看待事物的全新角度,對照他們的身分卻又非常合理。
本片也誘使我思考了很多新觀點,很多台詞都引發了我的深思,在思考生命的同時也在檢視著「為什麼這些台詞可以讓我覺得好有道理,而我之前卻從未這樣想過」,因為這種在觀眾底線橫跳的特性,我也預期這將是評價兩極的電影,喜歡的會非常喜歡,不喜歡的會非常不喜歡。
說到poor things的sex場面,看到短評很多給了負評,所以很想反駁一下。
我不覺得這些場面很凝視的原因是因為我幾乎都專注在Emma Stone的表情演技上了,我看到的是她如何享受、如何學習、表現她感受的表情,所以不覺得很凝視,當然場面很露骨所以這有點見仁見智。
我認為性不是毫無可取之處或是需要感到羞恥的事情,性也是學習的方式,因為性,她接觸了世界上很多美好和醜陋的人事物,也讓她一步步去探索何謂活著、該怎麼活。
然後我也不覺得女性通過男性得到性高潮是錯誤的事情,貝拉基本上是把男性當成發洩工具或是學習用品,是她探索快感的玩具,她也不汲取或渴求這些男性的愛,她去當妓女也只是因為她剛好需要性也需要錢而已,並不是為了討好或迎合那些下流的男性。
甚至貝拉也不是只因為男性的性行為而得到快感,她自贖、跟女性親密接觸也能得到快感,她的性快感不是建立在她需要男人上的。
貝拉所做的抉擇都是因為她自己的意志驅使,她是純潔的、不受任何社會道德的規範,她的所作所為都是她想要去發現、想要去挖掘自我,所以在意識覺醒後她是真正自由的,不受任何人擺佈。
她確實當了妓女讓男人得到了快感,但並非其本意,她始終是為了自己,她透過性跟冒險去接觸不同的人和環境,靠著閱讀與實踐來提昇能力,以探索活著的真諦,那就是為自己而活,不被束縛的、自由自在的。
話說我本來以為繞一圈回到英國後,結婚典禮結束故事就要準備結束了,沒想到來了一個回馬槍,讓我們了解貝拉的過去的同時,也跟現在的貝拉成為巧妙的對比,瞬間讓電影的層次更加豐富了,雖然結束在結婚找到愛的真諦也行,但這樣確實有點浪費前期的鋪陳,導演也沒讓我失望,這一段讓人印象很深刻。
曾經的我不開心所以放棄了活著,但新的我找到了活著的樂趣,所以我雖然不怕死但想要活。
值得一提的絕對是電影的美術設計,品味太好了,倫敦依舊是倫敦、里斯本依舊是里斯本、亞歷山卓依然是亞歷山卓、巴黎也依然是巴黎,但被重塑成了夢幻、美麗、超現實的模樣,很符合貝拉探索世界的視角,或許真實世界不浪漫,但天真、未經世俗污染的貝拉看到的都是新奇的、引發她的好奇心的。
片中的黑白鏡頭和魚眼鏡頭的設置也很有意思,目的是讓人專注在「人的行為與表情」,而非對話或血腥的場面,防止觀眾注意力被拉走,也達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讓影片很有藝術感。
電影因為貝拉的低幼以及不受到道德規範的自由所以充滿黑色幽默,還蠻可愛的,很多人笑了,本片確實是黑色喜劇,報名金球獎音樂與喜劇片現在看來非常正確。
這是一部成長電影,觀影的同時也是跟著貝拉重新檢視自己,跟著她一起重新學習生命,把自己當成白紙從頭開始。
整體來說觀影體驗很好,感覺時間很快就過了,總之還是蠻推薦的。
如果覺得這是男性的意淫或是女性的自甘墮落,那本質上你的思維跟電影裡的男性無異,你並不適合看這部電影,談性色變不是什麼好事。
還有一點是,只有在貝拉的靈魂感到自由時,畫面以及世界才是彩色的,我想是不是導演有意為之呢?
ps:雖然還沒看過所有奧斯卡入圍作品,但希望Emma Stone二封!
她真的非常精準的掌握了不同時期貝拉的表現,尤其是表情演技很細膩,一眼就能看出來前後期的貝拉有多麼不一樣。
9 ) 我尋思這跟女權有啥關係?
繼《巴西》《布拉格狂想曲》還有其他已經說不出名的B級片後,首部再讓我有驚喜的年代模糊作品。
時代和服化道僅作為表達的工具而不是背景,讓這部片子不拘於單一時代觀念的表達。
讓我非常意外的是,無論是這部片子豆瓣官方的簡介,還是大部分的熱評/冷評,居然把片子定位為女性主義/女權主義覺醒篇。
且不說這種以偏概全甚至是張冠李戴,有位網友說得好,好像現在影評人/觀影者不把帶有性場景的解讀扣上幾個俗套的、陳舊的學術名詞,就生怕顯得自己看不懂。
不禁懷疑,這些影評是不是壓根片子也沒看過,純粹是把影片簡介和幾個“女性主義”關鍵詞鍵入GenAI工具,讓他腦補一篇格式化的影評。
言歸正傳,近些年來,都算不錯的保持著觀影前不看影片劇情介紹的習慣,(不過現在看來,應該被像這部片的簡介誤導而去看片子的時刻也很多)觀影後的第一感覺,當然是不免俗套的是一部奇觀電影,但導演/編劇的高明之處在於,在很多可以自以為是加台詞上價值,用蒙太奇上情緒的情節上,全都克制住了。
他給你裸露鏡頭、玩具化的解剖場景、瘆人的肢體殘障、維多利亞時代服化+飛船+AI渲染風格假氣象,他的目的與常規的奇觀電影相反,他不是來引起觀眾性慾,不是跟發條橙一樣為了讓觀眾產生心理和生理的戰慄,他給我一種“it is what it is”的從容感,性就是性、腦子就是腦子、怪物臉就是怪物臉,他們就是表達的對象,不是手段。
這種intention跟主旨是不謀而合的,片子主線我認為是講一個人如果身體成熟但心智與初生兒無異,ta認知世界的進程是怎樣的。
這個主線藉由一個外科手術狂人的實驗進行交代,敘事也緊扣著外科手術(我理解為環境等非超驗元素)如何影響意識(認知世界的方式)進行。
出發點無異是獵奇的,這一點狂人也承認,此舉為推進外科醫學的作用是再次不過的念頭。
在這個成人身體成長的嬰兒認識世界的過程中,遇到的這些風格化的工具人分別代表社會上主流的觀點和元素,助推主人公進入the real reality:作為經典男權代表的Duncan(意外地有真情哈哈,但仍然是出於私有化的佔有慾,跟養個芭比娃娃似的那種寵愛的目的)、理想伴侶Max(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用俗人的經歷和語言其描述一個這樣基本不存在的人,他能從純意義而非象征意義解讀本次的whoring的原因,重申,是本部影片的whoring不是各種情境下的whoring,來自於純粹的意義探索和尋歡作樂本能,並不會如Duncan一樣聞whore喪膽)、父權制的代表Godwin(囚禁控制“女兒”,像動物訓練一樣;還有微乎其微的溫情:睡前讀圖書的cliche)、the wise的代表Harry和Martha(通過完全“叛道離經”的大膽交談讓Bella能依舊用破碎的原始的語言結構和遣詞造句去進行直擊心靈的問答,只有在他們這裡Bella才真正被啟蒙。
Harry帶Bella看貧民窟這個情節我很喜歡,因為無論是觀眾還是劇中人其實都沒有誰會完全相信世界上存在如Bella一樣“不諳世事”的、原始的、純粹的人,給她點“顏色”看看一個是想拆穿她是否偽善或者矯揉做作,另一個也是一種苦媳婦變惡婆婆的邪惡動機,這一點Harry自己也親口承認)、還有社會上最典型的最容易冒充人生導師的老油條鴇母,所幸Bella並沒有被她編織的“whoring-living”充要條件邏輯陷阱圈住。
其實講到這裡,已經足夠體現這部片子不是什麼女權主義/女性主義(這篇不來討論名詞的區別和無意贅述性別主義麾下這些已經老掉牙的理論)的立意了。
如果鴇母沒有說出那番“苦口婆心”的話,我還能勉強理解1)性自由代表解放(同樣無力吐槽為什麼性自由不代表解放因為本沒有自由這個簡單道理了);2)性場面就是男凝這部片子是剝削女性。
但導演已經借鴇母之口交代了他對1的觀點了呀...而且是完全相反的觀點,網友到底是怎麼總結出來導演在推廣性自由代表女性解放的..至於2嘛,我還是得沿用剛剛的立場,這部片子給我最好的觀感在於他的所見之物就是所見之物,不是用來arouse其他事情的媒介。
不過還是得承認,性場景在這部劇中的作用,我覺得主要是1)不可免俗地想要賺噱頭,畢竟好萊塢大明星三點全露(這裡勉強同意網友提及的對女演員“性剝削”)2)Bella作為一個擁有成熟女性身體在性器期的探索(反正我看了之後一點都不覺得香艷)3)因為成熟軀體的存在藉由性器期加速進入青春期時,對於生產資料的認識(就是whoring那段,其實通過跟這麼多連Bella都親口說我不喜歡/也不舒服的男人的交媾場景,已經很明確無論bella還是導演都清楚的知道whoring根本就不是女性天賦的生產資料優勢...那班說女性解放的人是不是現代鴇母...)最後總結一下,我覺得這部片子不是“女權主義”的正/邪片(真的救命,這種在我讀初中時候就已經老掉牙的東西為什麼過了十幾二十年還被當成寶啊...看點新的理論也好啊)的話,那他講了什麼呢?
我覺得是一個探索人之初的實驗故事:如果一個不加引導的孩子進入花花世界,他是怎麼理解、怎麼表達、最後選擇怎麼生活的。
估計直接用小孩子身軀的小孩子去表達一個可能會違法另一個演技上也難以調控(畢竟電影相較於單純成長錄影帶還是得有節奏有焦點,就拿re-enact小朋友牙牙學語用詞混亂這一個設置來講,還是成年演員把控力更強吧,並且還能營造一種與年齡不相稱的奇觀美感),影片選擇通過成年女子孩童化來表達,通過典型人物的設置,讓觀眾能直觀看得到世俗各人眼下一個有著和年齡不相稱的純真思想的人會有怎麼樣的境遇,成年觀眾去看一個看似像精神病患者卻實質真的是孩童的成年女子如何認識世界,應該會比直接看小孩能獲得共鳴和感到錯愕得多,還增加了詭譎的氣氛。
而這正正是作者想要帶出來的:我們作為觀眾其實跟片中各類路人的反映一樣,我們“本能”地拒絕一個童稚化的成年人。
反正我個人挺買賬這種反差設置,你會更直觀地看到同情、直白、喜形於色等與生俱來的品質是如何不被成人世界接納的,但在現實中的小孩子身上卻可以。
所以我們不被接受再保留“小孩特有”的品質究竟原因是什麼呢。
所幸,作者如剛才所說,沒有藉由任何一個人的台詞給出答案,這正是片子美妙所在。
唔,怎麼越發覺得是一個精神病(不要跟我argue這個詞在這個地方的定義,此處取一般定義)患者獨白的故事了。
唯一不足的點在於主線外的觀點表達有些零碎又不太捨得去掉,譬如狂人之所以成為狂人多半歸咎于變態的外科醫生父親和從小到大“孩童對於父母就是私有財產”的觀念侵害,這個還是比較顯而易見而且相較於本片主題來講也不如不講(贅述,不太需要Godwin太多自我剖白的環節)了。
另外幾點瑕不掩瑜的細節也想吐槽一下:這種章回式的結構和美工形式怎麼看著這麼像indie或者大學生視頻論文的結構哈哈哈;最後那段斯德哥爾摩的不捨鏡頭大可刪去...還有畫面的東歐風情美學、若隱若現的意識形態元素,感覺加進來就比較雜了,但我懂的啦,要我是作者,想要做競賽單元,也會想把所有想表達的都盡量放出來,雖然成果就好像我的論文一樣堆砌...
10 ) 男导演是不是真的拍得不好,女导演是不是真得拍得好
出片源那天就看了,但是到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说实话我不觉得任何与女性主义有关或女性议题的电影可以达成某种令女性满意,理解并诉说了她们的处境,并且不是某种僭越的代言,不感到女性在影像中被剥削凝视(比如这部电影得到的评价),并同时令男性觉得这电影不是因为是女性拍的/是女性议题,而是因为其本身(这本身存在吗?
)所以值得称赞(比如芭比得到的评价)的结果。
有吗?
就像我本人对于女权主义运动持有悲观态度,所有的事业都是为了那个不存在的乌托邦之前的挣扎,尽管这事业是需要做的应该做的。
如果女性走向解放的电影需要一个结局,那么我不觉得这会是一个美好的,并且男性也认可的好的结局,因为这有助于女性的生存而不是又多了树敌之危(如果女权主义选择的路不是让男性全部灭绝的话),这也和电影是一回事,如果人们一定要求电影对这个世界的现实负责的话。
如果为了吸引女性观众,复仇剧也许是商业上最可行的,这部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此类。
囚禁女主的前夫被俘虏成为某种低贱于人类的生物(羊?
)并可以被随意使唤,这应该比直接杀了他更令人欣快。
但是显然现在的观众(女性观众)已经不满足于这种荧幕里臆想成功的自嗨了。
对于这样的电影,人们一定会批判虽然问题矛盾现状困境确实被提出了但是最后都还是要变回包饺子而现实依旧什么都没有改变,言轻是无视真正的问题逃避现实缺乏勇气,言重则是企图用影像世界的乐观主义来掩盖甚至否定现实中的困境。
所以现在变成了男性导演拍女性议题的电影就是不可能理解女性的库切式质问你不在那儿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女性导演拍就是只要是女的拍的就应该鼓掌叫好吗的两难局面。
总结一下,问题就在于,男性导演是不是的确拍得不好(就算不考虑什么剥削女演员兰斯莫斯这电影也一样烂!
)而女性导演是不是的确拍得好(即使不是因为女性主义的标签和商业上的大成功格导这电影也一样好!
)写完这句话,我的悲观尽在其中了。
始终,我们还是陷入了论证我们这个性别的好,而另一个性别定不好这样的困境里。
还是说从本质上而言,两性之间是无法互相理解的,所以男性导演即使拍任何有关女性的电影,都会是某种程度的曲解和想象。
而女性的电影即使在各方面都是非常平平无奇的,但是因为是女性电影,是女性有关自己的话语,所以总是有意义的?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而心里有答案的,实际上也不存在一部电影让他们改变这个答案。
电影这种娱乐产品(在兰斯莫斯这儿我不想称之为艺术)显然不能解决这种从伊甸园肇始的问题。
电影就是一个拳击场,有的特别激发人们的战斗欲,可能就相当于裁判喊了几句煽动性的口号吧,然后人们闻声而来,在这里进行他们已经进行了无数次的,没有分数胜负的战斗。
不过对于裁判来说,打得越凶,他看得越爽吧。
他可不会下去拉架,或者裁决谁胜谁负的。
如果一定要尽可能行排除与之有关的性别争议来从其“本身”评价这部电影,就我自己的观影体验来看,也只能算是合格的娱乐片,我说的合格的意思是,人至少有欲望看下去,兰斯莫斯之前的某些电影我没有看下去的欲望,因为是一种浅薄的disturbing。
虽然说是拿了金狮但是毕竟戛纳都给《钛》这样的东西金棕榈了所以也没什么,再说现在三大和奥斯卡基本是一回事了,顺祝石头二封。
从视觉奇观来讲,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God解剖课的教室,吃饭时候的胃液插管,半鸡半猪的不明生物,里斯本和游船的诡异布景,以及每一部分衔接处的超现实主义慢镜,虽然远比不上拉斯冯,但是比他自己以前那种毫无意义的慢镜头还是有所进步的。
音乐尚可,和影像的结合很恰切,在这一点上,是完成度非常高的。
至于兰斯莫斯本人,他已经对高概念寓言形成了路径依赖,从《狗牙》《龙虾》《圣鹿之死》到这一部,以至于我觉得他除此之外已经不剩什么。
鱼眼镜头和圆形窥视视角的出现让我摸不着头脑,可能还没有理解到兰斯莫斯的良苦用心,但是这电影也不值得再看一遍去领会了。
Sex scene过多,和Mark Rufflo的那一段我倒是的确感受到了那种furious jump的气氛,这有助于我理解这些情节的必要性。
小孩子喜欢上干什么事就毫无节制地干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Rufflo演出了小丑的感觉,十分可乐(但是请问这位大爷跟帅有什么关系)但是后面在妓院的那种极其浅表的“体验”生活和对于招妓者的怜爱和共情让人感受到断裂。
老鸨对女主指点的话语没有展现出这个身份的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复杂的张力(这点请看今村昌平《日本昆虫记》)这也是高概念玩多的后果,所有的逻辑和感情都禁不起仔细的琢磨(当然有人会说你懂什么这是希腊诡异浪潮陌生化间离云云,但问题是他这部没想走这个路线)那种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中都暗含着真实情感的流转的电影,现在几乎绝迹了,所以也怪不得兰斯莫斯。
日本昆虫记 (1963)8.31963 / 日本 / 剧情 / 今村昌平 / 左幸子 吉村实子这部里有女主角在教堂遇到老鸨被招去当妓女然后到自己当上老鸨的过程至于故事本身的设定,就别算在导演头上了吧。
我看了一下,他没参与编剧。
兰斯莫斯挺好的,理解有人喜欢他,但是最好的那些导演就是兰斯莫斯这样的了吗,那也不太好。
所以先别说它好,万一以后有真的好的呢?
还是要抱有期望的,那真正好的一定有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结局。
最后比起有更多拍“很好的”女性电影的导演,我还是希望有更多在现实中尊重女性但是拍烂片的导演。
这比拍一百部女性主义电影都对这个世界更好。
如果两者都有那自然是最好的,虽然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也烂片也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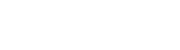












































































希望是爽剧,因为对元真儿有好感。这姐真的缺爆剧,唉。
七分,与明星大侦探《x学校杀人事件》那个案子异曲同工,父母(或者说监护人)欲望期待扭曲了感情的本真,四个青年各有各的苦楚,演员都不错,就是不知道剧情往爽还是往深里走了。
第一集就让我看生气了dex还是别演戏吧
地下赌场看场子的不带枪吗几个小屁孩冲进去胡闹?题材略微有点扯看不下去
蛮有看头的 元的演技比我上次看她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