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里卡奇遇》剧情介绍
艾萨克(利卡多·特雷帕 Ricardo Trepa 饰)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一天,他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电话那头的,是当地十分有名的富豪之家,他们向艾萨克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请求,那就是替家中早逝的小女儿安杰丽卡(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 Pilar López de Ayala 饰)拍摄一副肖像。 艾萨克接受了这个充满了不详气息的委托,然而,当他亲眼见到安杰丽卡之时,却立刻被其完美无缺的样貌所俘获,他根本就不相信,眼前这个双眼紧闭一脸安详的的少女早已经香消玉损。之后,更为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艾萨克镜头之中的安杰丽卡复活了,她化身成为不散的魂魄,日日缠绕追随着艾萨克。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回乡逗儿友情以上溺水小刀六号关口外星圣诞劫灵异妙探第一季远漂成曦曲偷得将军半日闲发明家用我的生命去爱你平安夜校花朵朵宠上瘾血浓于水等云到掮客小小的我诺桑觉寺超级的我少狼第一季鬼灭之刃锻刀村篇异搜店神勇佩塔反击第三季两极对立探险迷局边境攻略要加热这份恋情吗?假证人旭东
《安吉里卡奇遇》长篇影评
1 ) 仅能领悟其“器”的层面
追随 亵渎电影 看了此片。
故事很简单也很整齐,貌似是半个人找到了另半个人因此获得了圆满,进而飞升,无关乎生死。
个人很难从“道”这一层面完全领悟此电影,百岁老人,宛若一片深泽,未敢涉足。
只能从 器 的层面加以欣赏。
很欣赏导演细腻的叙事方式和镜头切换。
值得提及的有两处:一处是雨夜找人拍照:雨夜空街——有车驶来——叫门灯亮——完事儿灯灭——汽车驶离——雨夜空街。
一个个分镜十分的整齐简练,甚见功力。
另一处乃是结尾,房东太太拉上窗帘,关上法兰西窗,光线暗下,关门声,字幕。
很富仪式感。
其实“事实”“叙事”“故事”乃是三个相互牵扯的元素。
“叙事”作为桥梁和过程连接了两端,叙事的方式亦值得关注 器物 的我(们)着磨。
更深层次的,着实未参透,正如看了 生命之树 后欲言又止,无言以对一样。
2 ) 小众,有些深奥的东西,个人喜欢
很小众的一部电影。
首先是里边有关于vintage 的一些事物,比如房间布置,家具陈设,以及恰到好处的背景钢琴曲。
其次是男主的外表和气质,喜欢这种不是明星的有味道的人来出演。
高能的是里边讨论反物质,能量,精神的那一段。
总有人会悟到这些超现实的东西。
出体的那段颇有感觉,清明梦的情景展现得比较到位。
“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讨论死亡、物质与精神的存在,很有意思”。
小众预示着评分会低。
但是不会阻碍喜欢这种特别的调调的人,细细品尝。
3 ) 恋物的极限
恋物的极限[安赫利卡奇事]O Estranho Caso de Angelica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主演:利卡多·特雷帕/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利昂·希尔维亚/菲利佩 瓦尔加斯出品:法国Epicentre Films片长:97分钟媒体评论:奥利维拉可爱又悠闲地歌颂了浪漫,并在CGI的时代,制造了一出仿古的艺术品。
《华盛顿邮报》这是一出不可能的寓言。
《村声》既是爱情,又是恐怖,奥利维拉的电影不仅仅是有趣,幽默和极富野心的,它还有着更多的阐释空间。
《旧金山纪事报》奥利维拉的电影在给予我们视觉美感的同时,还捎带有关于人生和艺术的有力反思。
《看电影》[安赫利卡奇事]是一幅古旧的油画,他不属于我们当下的时代,反倒更像是半个世纪前的作品。
他甚至比半个世纪的时间更久,因为他的内核,可以追溯到古老的艺术诞生之初。
这么说,虽然有些玄乎,但世界上最老的导演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其长过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本就应该有着超脱凡人的不俗体验。
而观看本片的同时,也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快感,一种是对于单纯视觉美的欣赏,一种是和智者哲人通过作品的对话和思考。
在这个越来越爆米花化的今天,奥利维拉用这样的一部电影,回溯的其实是早已被时代抛弃的古典修养。
本片中,奥利维拉提出了一个极其值得思辨的命题,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如此追随美丽,以及一个关于得不到爱情的宿命悲剧,短短90分钟的观影,向观众传达的,则是百岁老人对生活的执着以及对年轻爱情的眷恋。
其实,[安赫利卡奇事]已然超过了简单的恋爱,其将对美的崇拜,异化为恋物的讨论。
也许这份不计回报的爱,正是奥利维拉所追求的内心真实。
一幅油画的自我指涉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本片的视觉风格,那我一定会选择“如画一般”作为最终结论。
奥利维拉曾公开表示,如果不拍电影,他更愿意成为一名画家,事实上,在[安赫利卡奇事]中,他不仅仅做好了导演的本职,更展现了他极富经验的绘画构图。
闪耀的光线,毫无现代痕迹侵袭的乡间街道,以及基本处于静态,并没有太多走位的人物关系,都可以明显的看出奥利维拉电影和经典文艺复兴油画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
本片正如同大多数奥利维拉电影一样,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时代标志,看上去像是遥远的旧时代,但一些新款汽车的偶然入画或者人们讨论的实事话题,则又会让我们穿越到当下的生活。
确实,在[安赫利卡奇事]中,奥利维拉有意将时间背景抽离,营造了一种类型梦境的暧昧氛围,为影迷提供了一个可以躲避当下焦躁社会的途径。
不过,正如同[午夜巴黎]中所说的一样,每个人心中的黄金时代,都是别的时候。
而片中的男主角以撒,虽然生活在奥利维拉所梦想的旧日时光,却有着逃离现实的真切愿望。
而他所向往的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死后天地。
他渐渐的疏远了身边为柴米油盐烦心的普通人,被其照片中所拍摄的美丽少女安赫利卡的尸体所吸引,并且由于某些超自然原因,他看到画中的安赫利卡向他眨眼。
照片中她美貌脱俗,让以撒逐渐沉溺,并幻想其从照片中走出,带着他遨游太虚。
这样一个类似于《聊斋志异》的故事,放在不同的导演手中,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呈现。
[午夜凶铃]中的女鬼走出电视,是对这类题材的保守拍法。
而前不久让影迷大呼坑爹的[画壁],则从猎奇的角度,展现了不同世界的一瞥。
但对于[安赫利卡奇事]来说,奥利维拉显然不需要这般的哗众取宠,他更想展现的,是一出有关美的寓言。
由奥利维拉本人的孙子利卡多·特雷帕饰演的以撒,有着与《圣经》中差点被父亲牺牲的无辜儿子一样的名字,他所代表的也正是奥利维拉被世俗牺牲的年轻纯洁的自己。
这位摄影师,热爱拍摄劳动者的照片,向往安赫利卡的圣洁之美,显然是一位理想中艺术家的形象。
但他经常拍摄的葡萄园劳动者,则让人联想其奥利维拉本人所拍摄的第一部默片[多罗河上的辛劳]。
在这部1931年的小短片中,奥利维拉初持摄影机,如片中的以撒一样,对于一切简单的事物充满好奇,这一层移情,明了异常。
同时,在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以撒的生活也是平乏的,导演巧妙的借用了几个侧面人物,展现了这层枯燥的无知。
在以撒所住公寓的大堂,奥利维拉巧妙的设计了一个下午茶聚会,在这里,人们讨论八卦,讨论股票,并且讨论以撒是个多么古怪的年轻人。
他们还试图将以撒拉入自己的下午茶阵营,但最终却被只在自己世界活着的以撒所忽略。
他只在意安赫利卡的笑容,如同奥利维拉只在乎电影一般。
最终,油画,少女和电影三者因为共同的美被导演巧妙的划上了等号,这也正是本片内在,最迷人之处。
一张照片的有力辩证戈达尔曾经由词源学的角度有趣的辩证了照片,图画和电影间的内在联系,说白了其实很简单,毕竟在英语中,它们都叫“Picture”。
而在本片中,如果你换一个角度,理解片中复活的照片,则就会发现更美妙的影迷意境。
其实,整个电影的创意,在半个世纪以前的1952年,便已经有了雏形,那时候奥利维拉便构思了一个有关于照片复活的故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加工,和断断续续的剧本创作,终于在如今开花结果。
一个男人迷恋画(照片)中已死的女人,并且渴望咋现实中追寻其而去的故事,其实在影史上早已有范本存在,而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希区柯克最富盛名的杰作[迷魂记]。
片中的金·诺瓦克在一开始所看的画像,正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死亡迷恋的最初意象。
他幻想着画中数世纪以前的贵妇,爱上了眼前这位所谓贵妇的后代。
并在诺瓦克假死后,要求爱的女人,装扮成死者的样子。
这样由恋物发展而来的爱,其实便就是我们爱电影的真正原因。
虽然奥利维拉本人并没有明说,但[安赫利卡奇事]却替他说出了心中所想,我们爱电影,犹如以撒爱上照片一样,迷恋的其实是逝去的时光和永留在胶片中女人的影子。
正如齐泽克所说,“残疾的女人才是美丽的女人”。
而奥利维拉正是巧妙抓住了观众的恋物癖,将安赫利卡这一角色演绎成了美之绝唱。
想象一下,以个真正的女人会是如何的絮絮叨叨,可能她会像片中的房东太太一样,八卦不止,毫无美感,或者她会像安赫利卡家的管家一样冷言冷语,难以亲近。
事实上,除了死去的安赫利卡以外,全片中所有的女人,都没有丝毫让人爱怜之处。
似乎,只有经过艺术加工的商业照片(电影)才真正赋予了女人独特的一层蛊惑美丽。
观众爱的永远不是女人的真实,他们只在乎女人美丽的形象。
也许,这便就是在狗仔发达的今天,再没有嘉宝那般银幕女神的真正原因了吧。
毕竟,细节越被无限曝光的女人,越失去其神秘的美感。
我们越追求美好,便越会在现实中受挫,这也正是[安赫利卡奇事]片尾,以撒逃离人世,任魂魄飘走的内在解释。
现实中无法承受的丑与银幕上触手可及的美之间,以撒和奥利维拉,都选择了最理想主义的纯粹。
事实上,如果联系起奥利维拉之前的创作,便可看出其对纯粹美丽的追求,其上一部作品[金发奇女]中,男主角为了追求梦想中的美丽女子,开始跋山涉水,完善自己,甚至得不到理解与亲人决裂。
但当他满心欢喜,迎娶新娘的前夜,却发现未婚妻其实有着偷窃的毛病,追求完美主义的他,无法接受,只得取消婚约。
确实,要么追求绝伦的人世间至美,要么孤身一人,独善其身。
这正是奥利维拉电影中的男主角所奉行的人生信条。
而这近乎强迫症的怪癖,在[安赫利卡奇事]中则变成了毅然迎接死亡的决绝。
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境界,已104岁的奥利维拉,其旺盛的创作力,可能还离人之将死的状态尚远。
他的作品虽以死亡作结,但依然有着偏执的生命力贯彻其中。
所谓向死而生,正是对其心态的最佳定义。
这面对死亡的从容不迫,正有让人释然的力量。
如今,奥利维拉的新片也在紧张制作中,让人有了怀疑,也许忘我的工作,也是奥利维拉极致恋物的又一种表达。
★★★★文/西帕克(原载于《看电影》特别加映栏目)
4 ) 诗
所谓一见钟情大概就是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大雨的深夜,Isaac被请去为刚刚过世的安格里卡拍摄遗像。
安格里卡安详的斜靠在椅背上,仿佛只是熟睡而已。
Isaac透过镜头,对焦的刹那间,安格里卡苏醒过来,朝他抛个媚眼,于是,Isaac不可救药的爱上了这个幽灵。
葡萄牙著名的导演奥利维拉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百岁高龄。
不得不说,他的镜头语言,显然已经过时了。
当Isaac第一次在梦中与安格里卡相遇,她们相拥畅游的时候,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百年前的默片时代,镜语一看就是那个时代方式。
虽然,画面匠心可见,声音也试图营造浪漫诗意的氛围,但是,技术的简单,甚至粗糙,还是很容易让观众出戏。
Isaac对安格里卡的思念和欲望,都是通过Isaac诗一般的独白表现出来的。
导演曾经拍摄纪录片,所以,电影中还是有大量的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包括对农业耕作的赞扬。
可敬的导演,但是,电影真的很一般。
比较,这种爱恋亡魂的电影,好莱坞有很多,拍摄的手法和情感塑造要精彩和感人很多。
咱们中国也有聊斋。
5 ) 很美丽的电影
很少遇见这么美丽的电影。
在我,用美丽来修饰电影是第一次。
简直像一场梦,不过电影的本身也只是讲一场梦而已。
特别喜欢以撒和安吉里卡在空中飞翔的那一段,好像以前读书时在美术教材上看到法国现代主义的一幅作品,名字叫做“吻”,还是叫做“恋人”什么的,画的是厨房里一对恋人悬浮在空气中,那男的像蛇一样扭过头来,吻在女人的唇上。
事实上,两人的姿体也都像蛇一样,也有点像飘在空中的丝带,双手贴在身上,整个呈现出波浪的形状。
那时候就觉得真是古怪而诗意的浪漫,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甜蜜。
电影中的两个人倒没有这般怪诞,多了一份冷清、幽深,只不过寂寞的意味还是一样的浓。
当安吉里卡在照片里突然向以撒眨眼,这个古怪的、年轻的女子那种可人的狡黠真是让人舒服而心悸;而当他们两人像一团白雾一样拥抱着,从阳台缓缓地向天外飞去,越过黑夜,轻快地漂浮在河流上空,微笑着,凝视着对方,或者打量着周遭的世界,这景致何其让人向往!
至于以撒从河水里捞起一朵花送给安吉里卡,则让我想起了戴望舒的诗歌。
戴的诗有这样的哀愁,但在这里还要浅一点,像浮在两人头上灰白的月光一样。
当然美丽的,不止这一个场景,例如城镇古老的风景,农民在葡萄地里劳作的场景,都很美丽。
不过这些是无关重要的。
假如按风景和人物论的话,我看过太多更美丽的电影,但是我不会说它们美丽。
因为这部电影真正有一种哲学蕴藉的美,它的怀旧色彩也像水底流过的一张黑白照片,若隐若现而一闪而过。
有些电影不但有美丽的风景和人物,也有内蕴的美丽,但不会这样纯粹而透明。
就好像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走在秋天的路上,内心有点小得意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这仅仅是一个方面——他不会告诉你具体的事例,他会以一件不那么曲折不那么像故事的故事来告诉你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也像一片黄色的树叶,你不知道它经历什么了,但你可以闻到它的清香。
有人说它精致小巧但内容浅薄,我觉得只是看起来浅薄,好像阳光照在水面,使人觉得水的清浅。
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是为了除了导演之外的任何人而拍,他是为了导演本身的愉悦而拍。
对我来说,它抓住了某种人生的本质,好像夏天午睡醒来的一阵恍惚,所有的人生都可以在这恍惚里窥测。
6 ) 复古的爱恋
奥利维拉在百岁之时拍出了如此浪漫,诡异,而又复古的作品。
油画般的画面,静默的表演,对逝去之物的爱恋在葡萄园里的工人和照片里安吉里卡的微笑中得以显现。
艾萨克在为安吉里卡的遗体拍摄照片时,美丽的安吉里卡在相机镜头里向他报以完美的微笑。
这是一个诡异的恐怖故事,但又如此妙不可言。
拍照是他的工作,相片是他的作品,如同电影之于导演一样。
安吉里卡就是艾萨克作品里的缪斯,如同安娜.卡里娜之于戈达尔,里诺尔.森威娜之于奥利维拉一样。
艾萨克爱上了这个完美的作品,同时,安吉里卡让他的作品变得完美。
艾萨克迷恋上了拍摄葡萄园里工作的工人,他忘我的拍摄这些原始的,挥洒汗水的一个个劳动者,随后将洗出的照片挂在房间里,一个个挥着锄头的男人与安睡的安吉里卡并排在一起。
艾萨克在睡梦中与安吉里卡拥抱着在空中遨游,飞遍天涯海角,他们如白色的幽灵般划过长空。
至此,艾萨克彻底的陷入了对安吉里卡的爱恋中无法自拔。
面对女房东在大厅里和朋友们以及其他房客关于各种八卦,现代科技,物理学理论的讨论,他漠不关心,他只一心念想着安吉里卡。
他在其他人眼中是个十足的怪人,异类,格格不入者。
他告诉女房东自己对现代科技和机械的反感,对人工劳作的痴迷。
他怀旧且质疑现代工具理性,他对逝去的年代和事物颇为痴迷,这似乎也是奥利维拉的心声。
每当他在梦里,在幻想中与安吉里卡相见时,总会被楼下的垃圾车发出的噪声打断,将他拉回现实。
这个时常出现的垃圾车声如此刺耳,这是现代科技特有的声音,是粉碎美梦的刽子手。
他看见女房东饲养的笼中之鸟死去后,疯狂的奔跑,大声高呼安吉里卡。
他似乎无法再忍受这个冰冷机械的世界,他要真正的和安吉里卡在一起,所以他死了,为幸福和那逝去的一切而死......他白色的灵魂跟随着安吉里卡再次从阳台上飞向天空。
他的遗体躺在昏暗的房间里的床上,房东为他盖上白色被单,放上十字架,关上唯一能看见阳光的阳台门,如同关上鸟笼一般......
7 ) 蝴蝶
很久没有这么有耐心的对待一部电影,啃了三天终于在看完音乐剧的夜晚站在无人的街道上默默看完。
百岁的奥利维拉气定神闲地用他油画般的镜头展现着古怪而诗意的古典浪漫,亦真亦假,颇有些庄生梦蝶的味道。
一直在想,是摄影师分不清虚幻与现实,还是生活在柴米油盐里的人们失去了能看见安吉里卡的眼睛?
摄影师迷恋的究竟是美丽的安吉里卡,还是纯粹的美本身?
柔美绵长的鸣奏曲让故事像极了八九十年代那些展现文艺复兴时期的老电影,可是汽车,机器,以及人们讨论的实事话题又把人拉回当下,一个古典美正在消逝的时代。
于是美丽的安吉里卡带着微笑死去,热衷下午茶的人们喋喋不休,机器代替了挥舞着镰刀的工人,笼子里的小鸟不再呼吸。
年轻的摄影师大喊着安吉里卡然后开始失去理智地奔跑,瘫在草坪上。
但是宣判他死亡的人并没有看到,他逃避了肉体的桎梏,时间在此静止,安吉里卡打开了天堂之门,他的灵魂在幻想里穿行,在白日里飞升......摄影师对安吉里卡的态度已经似乎超越了爱情的范畴,升华成为对古典美的固执的崇拜,永恒的追寻,以至最后他也变成了其中的组成部分,成为理想主义的殉道者。
这是他的蝴蝶。
8 ) 柏拉图主义+夏加尔
首先必须要反对某些影评当中对“恋物”这个概念的误用和滥用,恋物用《拉康眼中的艺术》这本书当中的定义是“展示和隐藏想象界菲勒斯产生的欺骗”,不是简单地用迷恋一个不真实的形象可以解释完全的,事实上恋物常常被用来解释迷恋人体的某个部位,而在艺术当中“一方面,我们在自身面前坚持语言能指的隐藏以使图画表象能适应现实中的预设表象,这些预设表象即我们愿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承认女人或男人的身份。
另一方面,在丢失了绝大多数的个人物件之后,我们心中仍会有特定的空虚残余。
这些原始物件未对发音清晰的语言或事视觉映像的表面构成屏蔽,但正是它们的丢失使这些表象成为可能。
作为表象代表的前身,它们使表象的模版在镜像阶段的时间和地点得以确立。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这部电影是柏拉图主义很强烈的片子,或者说具有浓厚的古希腊哲学色彩:非常强调灵肉二分,以及灵的超越性、自在性(但似乎没有达到自在自为的程度)。
而且这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涉及到灵当中善的部分,是以善之美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电影当中对农民劳作的场景作为美的描绘。
一方面,这种对于劳作的美学性质的强调似乎是超越柏拉图主义的,因为后者的灵更多的在于思的活动上,但是另一方面,劳作的美更多以善的面目存在于电影中,这种善和纯粹的美(安吉里卡)之美是有对立关系的(从房东对将二者的图像摆在一起的质疑可以看出这种对立),而这种善的维度放在柏拉图主义当中考察也是别有深意的,因为善在柏拉图那里是最高的理念。
但是柏拉图理念中的善实际上要更为宽泛和庞杂。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善的理念是超越实体(ousia)存在的。
而美、对美的认识和受到美的启发的灵魂这些都是在善的统摄之下的,所以在这部电影里美和善这对立的两极才能够打通。
柏拉图主义当中有一个比较硬核的理念在于,作为真正存在着的logos和理念是永恒的,而可感之物是不可能永恒的,因此作为美的理念的具现化的安吉里卡使男主徜徉于永恒之域,最终摒弃肉身离开。
另外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个画面和夏加尔这幅画构图的高度相似之处。
Over the Town,1918,Tretyakov Gallery, Moscow
9 ) 明月当空叫
大概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夏天住在姥爷家,姥爷讲过一个睡前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从前有个老头,儿孙都已成家立业,自己住在住了一辈子的旧家里。
他还每天都要干活,虽然干的都已经是不挣钱的,自娱自乐的活。
但是他每天干完活,还要在院子里挖个坑埋点东西,邻居们看见了,都很好奇他在干什么,但谁也没看见过他在埋什么。
原来是因为,有天干活时,老头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想让邻居把儿孙们叫来说说分家产的事。
但是当天夜里,却有陌生人向他托梦,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并让他不必把儿孙们喊来了。
于是第二天,老头告诉邻居不必把儿孙们喊来,并按照梦中人的主意开始行动。
行动其实很简单,老头在自家院子的树下挖了一个洞,每天都要挖出一些土来,过几天又会填上。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所有的邻居都在讨论,老头经常在院子里埋什么东西。
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老头的儿孙们先后回来看老头。
大儿子要接老头去养老院,二儿子要给老头请保姆,小儿子要给老头买电视机解闷。
但老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三个儿子全都搬回来,每天和老头一起做饭,大儿子一起做早饭,二儿子一起做午饭,小儿子一起做晚饭。
三个儿子全都回来了,真的每天陪老头一起做三顿饭。
这样又过了一些日子,老头死掉了。
三个儿子争执一番后一起去院里挖,最后挖出了一个高压锅。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和阿凡提传奇或者西游记差不多时代的故事,但其实在姥爷的世界观里,它可能就发生在八九十年代,那是讲故事时的当下。
过了小半年,我让姥爷讲故事,他又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几乎同样的版本,只不过院子里挖坑变成了老头他从房顶上拆下两块瓦当,在自己衣柜里腾出一口箱子,每天夜里睡觉前,都要打开箱子在里面折腾一番,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所有的邻居都在议论老头衣柜里藏了什么东西。
之后姥爷大概讲过三四个差不多的故事,也许更多不记得了,每次老头藏东西的方法都会有点不同。
姥爷的类型片之夏很快过去,另一个夏天我又去姥爷家住时,他又要讲老头藏宝系列故事,我就坚决不愿意再听了,因为从中根本不能听出什么寓意来。
“从前有个老头,他在院中劳作”。
二十年后我来到南方上学,这个故事偶或会被我自己梦到,于是场景又回到二十年前姥爷家的凉席上:每当夜幕降临,姥爷又开始讲述。
在度过了某种可堪忍受的无聊后,我就开始期待那个劳作不休的老头,这次要怎么藏他的奇怪的宝贝。
我一度以为姥爷潜意识中是在担心自己晚景的孤寂,但日常行事中的种种征兆显示,他显然已经超越了我这种浅鄙的思维。
那时的我根本不觉得姥爷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是在糊弄幼稚的我,我唯一的感受就是,姥爷真是太神秘了。
看这种片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以前的自己太土鳖了,以后还将继续土鳖下去。
如果没有经历过对上帝的信仰教育和怀疑,并不是就没有对归宿的思考和幻想,只是姥爷这种类似民科似的狡黠可爱,造就了一个对郭德纲古今传奇和奥利维拉cinematic情怀同时保持关注的我,种种混搭的土鳖审美,这才是我自己的安吉里卡奇遇。
10 ) 古典精神——《安吉里卡奇遇》
葡萄牙著名导演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2010年时已经102岁了,但他仍努力地拍着电影。
这位导演于1931年拍摄了纪录片史上的经典之作《多罗河上的辛劳》(Labor on the Douro River),此后一直在胶片上耕耘,历经默片、有声片、各国新浪潮,到今天仍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
1981年、1985年和1990年,奥里维拉先后获得了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
他总是将深邃的思索与电影结合一处,他的所有影片早已连接成为一片思想花园,而这新近的一部《安吉里卡奇遇》,是花园中一朵新盛开的玫瑰。
影片的故事颇奇诡。
一天深夜,一个年轻的摄影师伊萨克被请到帕塔斯家族的大宅子里。
家族主人新婚的女儿安吉里卡刚刚去世,家中亲人悲恸万分,便请摄影师来为女孩儿拍摄最后的容颜。
女孩儿死得安详,穿着华丽躺在椅子上,面带微笑。
伊萨克拍了两张,在近距离对焦于面孔时,女孩儿出神一般在相机取景框里嫣然一笑。
伊萨克即刻失了魂,疾速拍完,落荒而逃。
照片洗出来之后,伊萨克看到那张面部特写,那女孩儿竟又笑了。
伊萨克大骇,由此心神不宁,开始做诡异的梦,宛若天仙的安吉里卡从天上飞下来,抱着伊萨克在空中游荡。
奥利维拉以这故事与意象讨论了一个活人与一个幽灵的爱情。
这由心灵伪造的爱情极尽真实,却又极度幻灭。
就像影片中伊萨克在惊梦之后抽烟时领悟的那样。
影片画面中,香烟喷出后很快便消散开,“这是幻觉,却如此真实,就像烟一样。
”奥利维拉的画面风格一如既往地秉持着沉稳的艺术气息,所有的构图、人物站位、布光都按仿佛绘画一般一丝不苟。
这风格好似能将我们带往几十年前欧洲电影大师频出的年代。
借用《写意巴洛克》一书作者马慧元的一句话:“不是所有人都是时代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腐化的社会里埋藏着多么古典的精神。
”尽管这是写古典音乐的语句,但用在奥利维拉这曾经先锋,如今却古典极了的导演身上,恰如其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使用了大量肖邦钢琴奏鸣曲做配乐,且都由葡萄牙著名女钢琴家玛利亚-胡奥·皮尔斯(Maria-Joao Pires)演奏,这是影片画面之外又一不可错过的享受。
这两位艺术家已不是第一次合作,在奥利维拉1999年的影片《情归何处》(La Lettre)中,一个情节是一场小型钢琴独奏会,奥利维拉就真的请来玛利亚-胡奥,摄影机就端端正正拍摄了钢琴家的演奏。
■《安吉里卡奇遇》The Strange Case Of Angelica (2010) 国家: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巴西导演:曼努埃尔·德·奥里维拉Manoel de Oliveira主演: 碧拉尔·洛佩兹·德·阿亚拉Pilar López de Ayala 、里卡多·特雷普卡Ricardo Trêpa等类型:剧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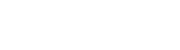






















【8】庸俗地讲,这是一个《画皮》里没遇到道士的王生的故事;形而上地讲,这是围绕摄影术的思辨问题。巴拉兹重视的“可见性”、德吕克的“上镜头性”、本雅明的“灵光消逝与机械复制”、拉康的“实在、象征与想象”、“摄影师是画家还是雕刻家”……种种复杂命题的蛛丝马迹,在情节简单的本片中皆有迹可循。我印象最深的两处场景:一是空中飘浮,宛若夏加尔的《小镇之上》;二是镜头掠过13张悬挂的照片,犹如电影中被抽取的13帧,农民与女子的图像间插着,像是被组合的蒙太奇。
室内构图很美。全片都在追逐 自然的 质朴的美。缅怀那些旧式的 逝去的过往,
Isaac第二次被Angélica的復生震撼的那一幕,祂從一個晦暗封閉的房間轉身步向農民們的葡萄園,生者的活力幾乎是僅此一次地照耀在牆面上—此後再難見到這般的沈溺與夢幻,即便祂一次又一次地凝望著城市與山脈,現世的污濁與粗鄙已經很難為這場皮革馬利翁事件畫上終結,唯有神的吟誦可以重新將柯爾律治之花送還那個永生的萬物王國,攜帶著虔誠的魂靈。 它同時也是唯物的,在黑夜中逝去的赤胸朱頂雀虛弱地道明
4.5。当摄像机的快门被按下的一瞬,一个画面就此定格,可这便是影像的全部吗?——它们会在想象的世界里自由地绵延,就如相片中挥舞至半空的镰刀会继续落地一样,笑容的永恒也超越了生命与死亡的界定。看奥利维拉的这部电影,像走进一张张油画,走进这些画面绵延而成的世界;静态的情境缓缓洇开层层涟漪,这是宁静的时间与空间和它们容纳的一切为情绪、视线与话语所牵动的难以言喻的古典之美。
第一次看奥利维拉,构图和用光很考究,油画感十足;导演清楚地展示了拍摄电影的代价:摄影术即摄魂术/招魂术,将已逝的不在场的美定格为永恒的在场,势必招致幽灵的回归——而他却轻描淡写道:我仅是想留住旧日之美;同为潜在的元电影,结尾的处理(驻足于画框)和阿巴斯的如沐爱河相仿,关上门窗颇有辞别之意
已逝的少女再不会有缺陷,定格的风景才能凝滞成永恒,世俗的汲汲营营是如此的惹人厌烦虚耗生命,所有美的事物都是不切实际的,生而在世令人痛苦的矛盾就在于此,只有虚幻的精神世界才能令人解放。充满古典主义与神秘的美,对生的思考与死的理解,困惑与迷恋。部分场景真是非常有共鸣了。
87/100,关于“旧”的颂歌,在绝美影像下画内空间如梦般抻开,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精神飞越的起始。相机留存下了瞬间,却永久的摄取出了幽灵,用死亡和安吉里卡永远相连,我们拥有永恒。
摄影师给刚去世的美女拍遗照,莫名爱上了,最后灵魂脱壳死去跟美女灵魂走了。题材有趣新颖可以理解,但大量莫名停顿的画面,莫名的画面切换,莫名的无关紧要细节详细刻画,是为什么?肖邦配乐和一些噪音也不懂为什么,反而让人更没耐心看此片
百岁老头用一个个静谧的长镜勾勒出神祗。这片真奇葩!
美丽的鬼片。Issac曾被一个噩梦惊醒,梦里面耕地的农民都不见了,只有一部大型挖掘机。与此同时,他又拍下许多不可能拍下的照片,仰望着农民举起锄头当空挥下,像是死神为自己掘墓。所以他恐惧的是天使和死神如果都不再是人形该怎么办。对于他来说,形象(名字)即意义,如果她像angel,那么她必是angel。
“有一天我要把双手,抛给寂静但依然温热的泥土,我沿着天空攀登。”
奥利维拉是与我无缘了
色调的精美冲淡了过往奥利维拉作品内挥之不去的舞台话剧感,使其更具有油画质感。并极巧妙的运用对于绘画的心理学期盼,安吉里卡在片内等同于蒙娜丽莎,嘴角上扬的微笑恰如后者在卢浮宫中那一抹神秘,这个心理学上自我动态(一种感官上的笑起来)化现实的静止为虚幻的运动,而电影这一媒介恰恰使个人的虚幻变为众人的现实,我们看到了自我补全画面的真实出现,一种期盼心理的达成。相较于背后隐喻的绘画,摄影更为居前,作为“连续摄影”的电影,应用视觉留存得以产生活动影像的方式,动与静的差别成为瞬间截取与生命保留的区别存在,奥利维拉用“复活”这一设计凸显运动影像的至高无上性,当一排摄影作品与动起来的图像并列时,美丽现实化为狰狞表情与完美存留的对照,鲜明对比出了电影的优势。在这里已经不是现实渐近线的赞誉,而成立另一世界的开辟。
摄影师爱上死去女子的故事,由葡萄牙百岁导演拍摄。默片风格,节奏极缓慢,以肖邦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气质古典隽永。以大量留白引发对爱情和生命的思考,如庄周梦蝶般,主人公倚爱之力,打破物我和生死的界限,放弃易幻灭的生命,走向极乐之境。
3.5,遇见安吉里卡第二天那些拍的非常非常好,后面有点太着急了,102岁写了首新编神话的诗歌在裂开的现代都市,而这种创作后来也被一些导演继承了吧,但如此的魅力我好像没有get到
一种平实的浪漫,用一副古怪的画作呈现出来。对时代的爱恋,对美的追求和疑惑,对死亡边界的浪漫化。数码影像的材质里呈现的油画质感,甚至和电影的内容有了呼应。全片三个运动镜头:林间幽魂飞舞; 梦中拍摄农业机器; 最后在田间奔跑而倒下,让一个娓娓叙述的小故事仿佛有了灵魂。
讲的是男主,一个摄影师,喜欢农耕的方式,喜欢一个姑娘哪怕她已经死去。镜头掠过他爱的瞬间,照片里一锤头下去的力道和农夫拼命的脸,姑娘睡去的美丽容颜。爱的都已死去,他也该去见上帝了。导演近百岁了有自己的满足和值得,仍坚持古典的情怀和表达,坚持画面的美感和余味犹长的观感,上帝也会敬您。
6.5/10 没有感觉到强度。传说在相片里能够看到逝者。/当你观看得太多,你就离开了世界。
云里雾里,友邻都看懂了而我看不懂系列。
拍的是油画,过多的隐喻,导演沉浸在上世纪初的电影情怀中,过分的时代隔离,与其说这是一部电影,我宁愿相信这是一首诗